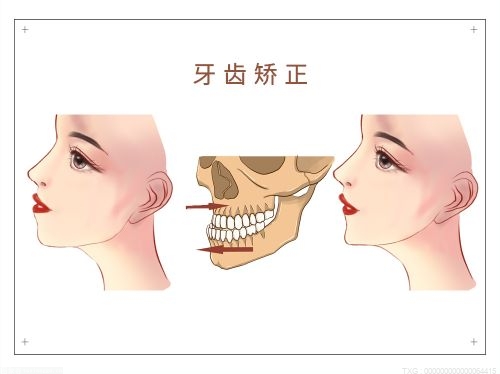《论语》十讲
为原书每一段话备注标引,给每一个标引词群集类分;
按照一定规则将大类排序,于是有了全新的《论语》。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第十讲比较
此篇取名“比较”,而不是“比对”或者“比照”,因为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对象可“对”、可“照”。
我学《论语》已经有几年了,笔记是纯手工逐字录入。参考对象有纸质的整本的书,也有网络上对某一段的解释。
今年参考的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简体字本),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16年重印。
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向以注释准确、译注平实著称,是当代最好的《论语》读本之一,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享有盛誉。
我拿我的笔记和该书进行比较、推敲,很受启发,有很多收获,进行了多处修改、调整,但同时也还存有很多疑惑。
我一直坚持,对《论语》的注解没有标准答案。我不想迷从杨先生,也不想让疑惑一直是疑惑,所以将我在今年学习中遇到的一些拿不准的地方列于此篇,希望能和读者们一起讨论、共求进步。
【为政】
13.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请教行政治理方面的要领,孔子给出了四个字“先之劳之”。
“益”是增加,“请益”就是请老师再多说点,进一步解释。所以老师又给了他两个字“无倦”。
无倦,就是勤政,兢兢业业,吃苦耐劳,无怨无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而不能尸位素餐。
劳之,也是勤劳的意思。如果把“劳”解释为役使,把“劳之”解释为“役使民众”,那只说一个“先之”就可以了。
先之,就是身先士卒,做出榜样。
先之劳之,连起来用,就是带头先干、带头多干。
{杨伯峻先生将此句中“劳之”译为“然后让他们勤劳地工作”。}
【为政】
13.2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有司:就是“有关部门”,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
仲弓给季氏当管家,也拿行政治理方面的事问计于孔子。孔子说了三条:给下属官吏做表率,宽以待人,提拔优秀的人才。
所谓“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一般人都是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当领导的如果管得太严,眼睛里不揉沙子,则无人可用。
前两条好理解,仲弓追问第三条怎么做?孔子分开来讲:你所了解、熟悉的,要举荐;你不了解、不熟悉的,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别人否定了的,你还要亲自考察一番。
“举贤才”的前提是“得贤才”,就像孔子问子游“得人焉耳乎”。“尔所知”亦即“得人”,是当官的一项基本职责。
你所知道的总是有限的,但只要你确认过的,都可以举。你不知道,孔子又分成了两类:一是没有定论,既没有肯定的评语,又没有否定的评语;二是有定论,有人说不好的话。这两类人都需要你亲自了解、把关。
{杨伯峻先生将此句(后半句)译为“提拔你所知道的;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埋没他吗?”}
【为政】【正名】
13.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名:名称、名分。
正名:表面理解就是纠正在名分上的用词不当现象。
阙:通“缺”,存疑。
错:同“措”,安置。
苟:马虎、勉强。
子路对孔子说:“卫国君主等着您去帮他治理国家,你就任以后打算先从哪儿着手呀?”孔子说:“当然是先得正名分呀!”
子路快人快语,心里怎么想的,嘴里就怎么说:“您真是这么想的吗?那也太迂腐了吧?干吗非得正名分,弄那些虚头八脑的东西呢?抓财政大权、抓人事大权、抓军事指挥权难道不香吗?”
老师要不怎么是你的老师,你不理解老师很正常,你可以放低姿态请老师给你细细讲解呀,但你公然质疑老师不就是找骂吗?!
孔子大怒,指着子路就骂:“你真是太放肆、太无礼了!君子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大概会采取保留态度,而不是乱下评论。”
下面的话是孔子的施政纲领,强调礼乐刑罚必以”正名”为前提。
如果名分不正,那么就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不能以理服人,事情就不能办成功;如果事情办不成功,礼乐教化就不可能顺利推行;如果礼乐不能推行,那么刑罚就可能出现偏差;如果刑罚做不到公正,老百姓们就会不知所措。
如果没有名分,你算老几?我凭什么听你的指挥?!所以,任命也是正名的一种形式。在正式任命文件里,正职就是正职,副职就是副职,不能瞎写、乱叫的。不仅职位要写准确,职责分工,权限范围等都要注明和做好界定。
说,谁不会说,只有名人说出来的话才可以称之为名言,只有皇帝说出来的话才可以称之为金口玉言。
言不顺,就是不能有效沟通。如果不能有效沟通,政令不出办公室,那么事情肯定办不成。
事情办不成,温暖都解决不了,谁来听你谈什么礼乐教化。
礼乐就是古时候的规矩,做人做事原则性的条条框框。如果礼乐意识得不到推广,不能让大家都了解,刑罚全凭长官断夺,那么就不是法治,不是礼治,而是人治。而人治难免夹带人情,同一件事,官长A说对,官长B却说错,没有统一的标准,民众就蒙了。
所以君子要想发号施令,必须先有合适的名分;要想政策得以推行,号令必须符合自己的身份。君子对于自己说的话,来不得半点马虎,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怎么说不该怎么说,都要符合既定的规则。我对我所说的话负责,我所说的话都有根有据,不是随便张口胡说的。
言之可行,是说言的内容是科学的,是遵从规律的,是符合实际的。言之有物,不说废话、虚话、空话。
名之可言,是说名正,有可言之名。你的名赋予了你言的权力,可以去说这些话,可以去颁布这些命令。你是一把手,你是负责人,你说了算。不是虚名,不是空位,不是“齐天大圣”,而是有实实在在职权的名,可以发号施令。
你子路,作为一个学生,不理解我的意思很正常,但你竟然敢质疑我,大放阙词,岂是君子所为?!
{杨伯峻先生将此句中“正名”译为“纠正名分上的用词不当”。}
【评弟子】【冉有】
13.14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与,4声,参与的意思。
孔子虽然在朝为官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名声大、影响力大。
孔门弟子在朝做官,需要事事向老师请示、汇报。有一次,冉有回来晚了,孔子问他怎么回来这么晚?(晏:迟、晚。)
冉有撒谎说:“有政。”即他在忙国君的公事。
孔子马上指出来说是“其事”吧?你是在忙季氏家的私事吧?
如果真是国君的公事,虽然我不参政,但我总有途径可以听说的。
礼:大夫虽不治事,犹得闻国政。
《左传》哀公十一年曾有记载,季氏以用田赋的事征求孔子的意见,并且说:“子为国老,待子而行。”
{杨伯峻先生将此句中“事”译为“事务”。}
【言】【政】
13.15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几:近。
莫:没有人。
鲁定公问孔子:“有没有什么金科玉律,‘一言’就可以让一个国家兴旺?”孔子说:“话不能这么说。如果非要找这么一句话,就是大家说的‘当国君难,当臣子也不易’。作为国君,如果清楚地了解当个国君的难处,从而都能谨慎、认真地对待国家和人民;作为臣子,如果都能体谅国君的难处,处处替国君着想,给国君抬轿,替国君补台,这不就相当于‘一言可以兴邦’吗?”
人心都是相互的,学会将心比心,方得人心。得人心者,国未有不兴。这句话其实说的就是换位思考,懂得换位思考的人,往往都是有大智慧、大格局的人。理解别人,就是善待自己。懂得换位思考的人,都有根植于内心的善良。理解多一点,苛责就会少一点;体谅多一点,矛盾就会少一点。
鲁定公又问:“有没有‘一言’可以让一个国家毁灭?”孔子还是回答:“话不能这样讲。如果非要找这么一句话,那就是大家说的‘我当国君没有其他的乐趣,唯一的乐趣就是没人敢违抗我’。如果他的命令是对的,没人敢违抗,不也很好吗?但如果他的命令是错的,也没人敢违抗,这不就几乎等于‘一言而可以丧邦’吗?”
呵,所以不要老想着当一把手可以“说了算”,说得对还好,说得不对,执行下去是要犯错误的。当了一把手,更多的应该想自己的责任,自己肩上的担子,举轻若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谢氏曰:知为君之难,则必敬谨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违,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邦未必遽兴丧也,而兴丧之源分于此。
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违,则忠言不至于耳,君日骄而臣日谄,未有不丧邦者。
{杨伯峻先生将此句中“有诸”译为“有这事么?”}
【评外人事物】【事】
13.22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南人”指南边的人。宋国在鲁国的西南,结合其它文献,大概是指“宋人”。宋人是商的后代,商人热衷卜筮。
巫医就是用卜筮给人冶病的人。
孔子引用了一句话,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恒心,是做不了巫医的。
孔子评价这句话:说得多好啊!正符合《周易》里“恒”的精神。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出自《易·恒》,意思是不能持之以恒地修养德行,半途而废会被人看不起,就要承受羞辱。
“不占而已矣”是说“这是告诉那些没有恒心的人是不能够去做占卜罢了。”
想做事、成事,光想是没有用的。得去做,一直做、一直做,才有希望做成。
{杨伯峻先生将此句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译为“三心二意,翻云覆雨,总有人招致羞耻。”}
【共勉】【君子】【小人】
13.23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不同的东西和谐地配合在一起。
同:相同的东西相加或相似的东西混同。
古人认为,相异相反才能产生和谐,完全相同只会产生单调。
君子是上层,重视和谐胜于平等;小人是下层,要求平等胜于和谐。越没有什么,越重视和想要什么。
孔子尚和不尚同,他讲的礼追求的是和,而不是同。“礼之用,和为贵”。
所谓“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奥;同作一文题,各自善其妙”,人各一面,从来都是参差不齐的,道德上的君子尊重人的不同,追求的是在一起的和谐,相互促进,共同成长;而不讲道德的小人则非要整齐统一,步调一致,共同进退,同甘共苦,同生共死。
君子尚义,大义之下,允许有争论;小人争利,此消彼长,安能有和?
{杨伯峻先生将此句译为“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
【共勉】【士】
13.28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愢愢,兄弟怡怡。”
子贡也问过同样的问题,但是孔子的回答是不一样的。
子贡是适合当外交官,所以孔子跟他讲的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
子路脾气不好,所以孔子跟他讲的都是搞好关系。
切切愢愢(si,1声):切磋勉励,是形容朋友之间的关系,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怡怡,是和睦高兴的意思,用来形容兄弟之间血浓于水。
孔子对子路说,先和朋友、兄弟搞好关系,才能称得上“士”。朋友之间勉励督促,兄弟之间和睦相处。
{杨伯峻先生将此句中“切切愢愢”译为“互相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