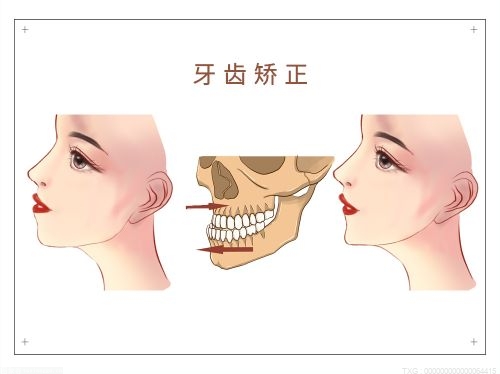文/谢新源
难怪人们常说要惜缘。有时一面之缘,竟能在我们生命的节点上烙下深刻印痕,令人永久地怀念。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2022年11月24日,文学大家李国文离世。我与李老师便有过一面之缘,那是我在北京参加文学讲座,听了李老师的一堂课。不足三小时的相处,却让我在23年之后记忆犹新。
1999年10月下旬,北京寒风凛冽,毫无预兆地下了一场大雪。解放军某部举办的文学创作培训班仍依时开班,众文学大家、文学理论评论家、文学编辑家应邀前来讲课。28日上午,我们迎来了李国文老师。
我们都知道他曾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因此个个欣喜不已。
当时,李老师已年届七旬,却精神饱满。他圆圆的脸上嘴阔鼻大,眼睛稍显细长,个头不高,宽肩厚背,与乡间普通老农看去并无太多差别。但他如炬的目光和既宽且深的额头,以及略显苍疏地向后背梳着的发型,却让人一看便觉得他是位睿智且有学识涵养的人。
李老师是江苏人,口音里却听不出丝毫吴侬软语。
他借用作家杨朔的话“相信自己的眼睛”为开场白,通过自己的两篇小说《童心》《月食》的具体创作过程,告诉我们一个作家、作者该如何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文学,在普通生活中去寻找特殊。
他说,广东作家陈国凯写过一篇名作《我该怎么办?》,一时模仿者众,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生活中的本真。这样模仿出来的作品没有一篇可以与《我该怎么办?》相比肩,而“相信自己的眼睛”正是自我突破的勇气之源。
这堂课上,李老师从不用一句文学理论术语来表达他的文学观点。他的话颇为幽默和形象,让我们在捧腹大笑中领悟到创作的真谛。
他说,文学的创作不只在于自信,更在于不停地写。搞文学创作要本着“狗叫的精神”。狗一旦发现了“敌方”,或者它认为有潜在的威胁,便狂吠不止,即便是狗主人也制止不住。
他鼓励我们既然选择了文学,就不能后悔、半途而废,要不停地写,相信总会有水到渠成的一天。
讲到第三节内容时,他一再提醒我们,创作不能搞实用主义,不能写什么看什么;要写什么,更要多看其他的什么。
当自己积蓄到了足够的学养,你的创作便如“发面”,会从一个小小“面头”发酵成大面团,蒸成的馍、烙成的饼才能叫人吃了觉得既甜又香。
他的创作体会就是,作家、作者必须拥有丰厚的生活,但这生活决不能是所谓的“体验”得来的。如此,我们方能在“创作中有创作”。
教室窗外雪花纷扬,寒风吹得营院中的古柏尖啸作响。即便是初冬,京城的冷已叫人畏惧。我们坐在讲台下有来自东南西北的四五十位业余作者,却个个都被李老师诙谐、高亢、有力的话语,说得热血沸腾、摩拳擦掌。
反倒是他的最后一段话,叫我们冷静下来——他语重心长地说,文学其实也是有四季的。四季轮回,当创作遇到像现在窗外的寒冬时,更要守着初心,寻找“冬天里的春天”。
《冬天里的春天》正是李老师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那部长篇小说。
讲座安排得满满当当,李老师则来去匆匆。自此以后,他在这堂三个小时的课上所给予我们的教诲却一直在影响着我。
现在,李国文老师已然作古,人世间却仍有他留下的作品和宝贵的人文精神。我也依然怀念着与他曾有过的这一面之缘。(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资料图片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易芝娜
校对 | 赵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