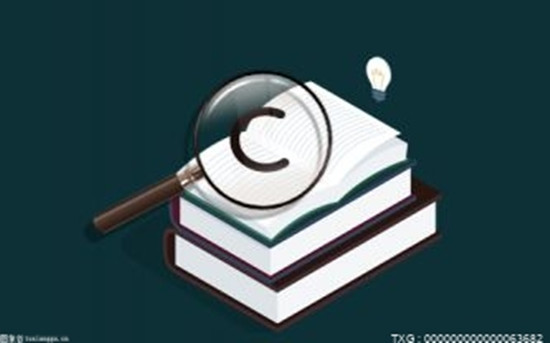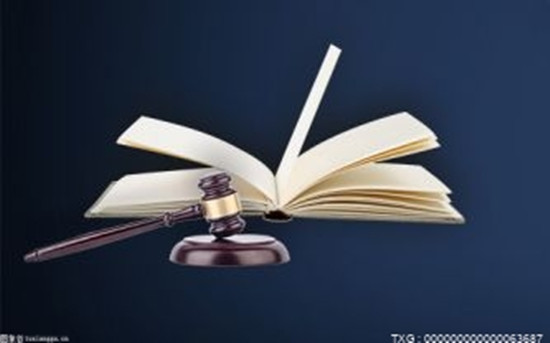一
我家老屋后面有一座山,不高,从山下到山顶,也就三百米左右。除了不高,另外也无名。无名不是没有名气,而是没有名字。虽然山没有名字,山顶却不甘寂寞。从我记事的时候起,这座山的山顶就叫闸山梁。山腰以下微凹,形成了一个小弯,临近山脚处又展出几块台地,有高有低,台地上错落有致地摆着包括我家在内的十来户人家。台地以下,是一大片庄稼地。秋天,或者冬天,会有一大群乌鸦黑压压飞来,然后黑压压地落在那一大片空地里,其间如果被什么惊动,它们又黑压压飞起,在天空中作短暂的盘旋之后,又黑压压落上闸山梁头。乌鸦的旋起旋落,很像上坟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烧化的黑色纸灰,密密麻麻和旋风一起升到空中的景象,有时给人颇为壮观的感觉。我小的时候看到这一幕,免不了会联想到很多,成人以后,则见怪不怪,甚至到了熟视无睹,没有感觉的地步。

(相关资料图)
对于闸山梁这三个字的因由,我以前全然不知。问起大人,大人们也不甚了了。于是因这三个字造成的困扰,在心中持续了几十年,一直到很久以后,偶然读到一篇文章,才知道类似于这样的地方,都是祭山的场所。闸山就是祭山,是旧时代人们惯常的一系列祭祀活动。所谓“闸”,在这里有“堵截”和“镇压”的意思,而所“堵截”所“镇压”者,无非天灾人祸而已。“山”则指的是山神。“梁”,在我的老家西海固一带专指山头,如“梁头”“梁顶”“梁峁”等等皆是。童年时候的我,经常会在闸山梁的周边看见一些瓷质的碗状物散落在杂草当中,很小,并且非常粗糙,据说就是当年祭山的时候埋起来的,后来因为风吹日晒雨淋,又陆续暴露在外,正好成了我读过的那篇文章的佐证。
闸山梁以东,有一道平缓的山岭,叫脚户梁。脚户梁上有一条小路一直通到很远的地方,那里有一座隆起的小山包,显得有些孤独和寂寞。以前把长途跋涉运送物资的人叫脚户,而脚户梁正好又处在两座古烽燧之间,所以其得名可能与此有关。远远望去,脚户梁除了一抹青草,还有一个不容易被人察觉的山洞,洞不大,仅可容身。洞中置放一门铁炮,炮身直径约半尺多一些,高约一米六七。我说不清司炮的人是谁,只记得天上起了过雨,电闪雷鸣之时,有人就会从洞中把那门铁炮移出来,然后对着云头发射炮弹。炮弹在云中爆炸以后扩散的热量会把聚集在一起的云团驱散,也可把云层中的冰雹消解,以防止其对农作物的危害。不过这种炮威力不算太大,遇上凶险的恶雨,往往起不了作用。尽管如此,但它却有一个威风八面的名字,叫铁将军。
闸山梁及所属的山下有一深沟,向北蜿蜒而去,叫苋麻沟。这条深沟毫无疑问是由雨水不断切割而成,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上万年的岁月,断不会有今天这样宏大的规模。沟两边的悬崖上,有自然形成的龛,或大或小,或深或浅,乌鸦多在其中做窝育雏。每当晨起暮落,乌鸦起身或归巢之际,只听得整个沟壑之间,叽叽喳喳,一片鸟语,分明另一个世界。
简单来讲,这便是我家以及我家所处的这个小村庄的基本环境,山上山下,一梁一沟,两相呼应,除过鸟事,剩下的便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人间。
二
在我的记忆里,就算生活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春天烂漫的花事仍然会给人以无尽遐思。尤其杏花,不仅开在人家的墙里墙外,连闸山梁这样干旱的高地,同样也会不失时机地占满枝头。而无一例外,这时总会有一个又黑又瘦满脸胡子的人动不动就坐在梁峁上。那人神情专注,很少说话,一旦坐下来,除了抽烟,还是抽烟。他不仅戴着一副墨黑的石头眼镜,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其实也像一块石头,如果正好有几朵杏花从身后斜出,再有一两只冒失的羊闯进来同框,则活脱脱就是一幅大写意的《三友图》。不过我到现在也不能准确地说清楚这个石头一样的人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大人们叫他“棒棒”,而我和我差不多的孩子都叫他棍叔。这个叫法有点特别,非得有个交代才可。且说叫他棒棒,由来并不意外,皆因这人每天爬山过沟,为了防身应付不测,随手总提着一根三尺长的木棍而得。在我的老家,大家管木棍常叫木棒,也叫棒棒。虽然在我所熟悉的语境中,棒棒之属必为木棒,而非木棒之外别的什么棒,如铁棒之类。但细细回味,木棒和棒棒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看起来可能和大小及质量有关,但有时候并不尽然。事实上就大小和质量而言,木棒和棒棒之间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所以木棒和棒棒的不同,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情绪和感觉所导致,虽然都为形而下之器用,但木棒显得坚硬冰冷,器用的特点更强烈,棒棒则显得委婉柔和,器用的特点被弱化。假如一个人用棒打了另外一个人,如果说用的是木棒,则有点严重,有可能皮开肉绽;如果说是棒棒,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颇有些云淡风清的意味。不要说人,就算说牛说驴,也一样,用到木棒,那是真打;用到棒棒,则更多的是姿态。按理,我们应当管棒棒叫棒叔或棒棒叔,却偏偏选择以棍相称,叫棍叔,叛逆的意味不可谓不强烈。
棍叔的职责是看山护林,除此而外,基本不参加其他的劳动。我这里所说的基本,是指棍叔不参加生产队里惯常的劳动,而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好像没有棍叔是不行的。关于棍叔有很多说法,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当兵的经历。据说棍叔十五六岁的时候,不意被一群散兵游勇捉获。那年月,西北一带兵荒马乱,长在地里的庄稼没有多少,靠打家劫舍吃饭的却不少。谁知那些散兵游勇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其实和土匪差不了多少,拿了棍叔以后没有多久,阴差阳错被一股来路不明的国民党地方军堵在前不见村后不着店并且夹在两山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差点集体做了炮灰,后经乞降,又因时局突变,才被收编。彭德怀解放兰州的时候,这股国军隔着黄河曾经和解放军对峙。这期间,棍叔蹲在坑道里不敢露头,他深信对面的枪子儿不是没长眼睛。当然也有不信邪的,如紧挨着棍叔的一个扁头不听劝告,非要伸出脑袋去看一看阵势,就听“叭”一声,大家还没有回过神来,随着一片血花落地,扁头已命丧黄泉。扁头的头顶有一撮白毛,被血染过以后红艳无比,活像一缕翻倒的火苗。旁边的人个个翻着眼睛,都倒抽了一口凉气。棍叔知道这一回碰上的不是软茬。虽然兰州一战打得异常惨烈,解放军的一方损失也相当巨大,但棍叔总觉得天下大势,早已翻转,成王败寇,不言自明,如果再耗下去,应该不是个办法。于是没等战斗结束,就星夜兼程,做了逃兵。
将近四百公里的路程,棍叔走了小半年时间,这期间的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可谓一言难尽。棍叔逃回来以后,老家已经是解放区的天了。虽然在旧军队里混过,但棍叔能弃暗投明,再加上祖宗八代都是穷汉,还是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分田分地之后,棍叔也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过一旦闲下来,棍叔却喜欢随手拿一截棒棒满山转悠。有人说棒棒在外面宽田宽地惯了,回来有点憋闷。由于棍叔的这个爱好,有了农业社以后,便被委以看山的重任,一看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管身累还是心累的时候,棍叔总会居高临下,坐在闸山梁的梁顶,有时看着山下,有时看着远方。
用现在的时髦说法,远方应该有诗。我不知道棍叔的远方是什么。
虽然棍叔是看山的,但在我的印象中总有一群羊若即若离,镶嵌在棍叔身后的山山峁峁之间,当然也少不了乌鸦,有时三五只,有时一大群。这也难怪,因为紧挨着闸山梁,就是生产队里的羊圈。放羊的人叫天亮。
生产队里的羊圈一般都建在山上,这样有利于把羊粪就近送到地里,免去了从山下送粪的艰辛。从山下看羊圈,看得最清晰的是栅栏一样通透的圈门。因为仰视的缘故,透过圈门看到的是天空和天空中的流云,而不是羊圈里的羊只,更不是羊圈那一面的高墙。如果是十五左右的晚上,天清气朗,便有一轮满月先从羊圈的圈门中升起来。大概是月色明亮的缘故,一根一根的栅栏几乎被消融得无影无踪,门框中只剩下一轮玉一样的光芒,然后一点一点朝向天空升起。这时候,假如碰巧听见放羊人天亮坐在羊圈一侧的台阶上吹一阵笛子,那种奇妙的感觉真的用语言无法说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被天亮那似乎能把人带到另一个境界之中的笛声所感动的,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还知道,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还常常听得泪流满面,只是夜深人静,无人知晓而已。也许是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人世间的种种深长的意味,等到我后来有点感觉的时候,生命中的那一幕确乎有些经典和不可或缺了。
因此在我的记忆中,天亮这个人物不是可有可无的。想想那几个关键词吧:羊圈、月色、笛声,而把这几样东西串在一起的,除过天亮,再没有别人。
那时天亮给队上放羊已经有十多年了,除了回家吃饭,他几乎完全和羊在一起。我后来外出谋生,每次回家,除了能看见坐在闸山梁上的棍叔,差不多还能看见天亮放羊的身影。然而,棍叔和天亮之间的互动似乎很少,两个人就像走在两条平行的道路上一样,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有所交集的。他们一动一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大山深处,凡是认真看过他们一眼的人,都会留下绵长的回味。大概一个人放羊,免不了会孤独寂寞,所以常常能听见天亮嘶哑着嗓子有一下没一下地在山谷中乱唱。山大沟深的地方,容易产生回音,天亮这一嗓子出去,如果加上回音,总得拖上些时间才能结束。有一回,天亮正面对着一条深壑唱得忘情,出于好奇,我悄没声息地从他的背后凑过去,谁料一转脸,天亮居然满脸泪花迎风横流。天亮有些不好意思,连忙收住嗓子,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抱怨风太大了。那一天的风的确有点大,天亮唱过以后本应该留下的一串回音,立即被吹得无影无踪。
不知为什么,我好像一直没有见到天亮戴过帽子,哪怕是冬天,也是如此。只不过冬天的时候,天亮留着长长的头发,到了夏天则把头剃得锃光瓦亮。我猜想,天亮之所以叫做天亮,大概和夏天他的头不无关系。不过这仅仅是猜想。天亮很小的时候惯玩的把戏是把一坨泥巴顶在光头上用手拍来拍去,别人不知道那一坨泥巴能干什么,天亮也不知道,所以拍到最后,别人不知道泥巴到哪里去了,天亮好像也不知道。如果有人问,天亮就用手在头上一阵乱摸,摸过之后,连自己也觉得有些可笑,明明顶在自己头上的泥巴怎么不见了?上世纪90年代初,单位派我到银川出差,中午上街吃刀削面。到了面摊跟前,就见一个四十开外的红脸男子,腰间绑着一袭花布围裙,头上顶着一坨面团,两把刀分持左右两手,然后拉开架势,面向一口滚沸的大锅,两臂轮起,立时便见两片刀如雪花在头顶翻飞,而刀口之上面条则如银蛇纷纷赴汤蹈火。我一时看得忘了吃饭,竟想起了天亮。
许多年过去了,假如天亮遇上眼前这汉子,不知会作何感想。
三
1973年,我老家一带大旱,一个春天都没有一滴雨。老人说,眼前这年景,要不是政府,不知已经死多少人了。那一年的救济粮从春天就有了,虽然刚开始领救济的只有一两户人家,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已不止一两家。日子一下子变得艰难异常。有人因棍叔见多识广,大概这天道轮回,否极泰来之数,也能说出一二,故以此相问。谁知棍叔双目一闭,双手捂住饥肠辘辘的肚子,不顾左右,不言他。来人无趣,只能敬而远之。
有人开始蠢蠢欲动,并且蓄意谋划了一次小心翼翼的灌山活动。为了防止被说成装神弄鬼、搞封建迷信,最后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秘密地实施了这个村子有史以来的天字第一号计划。
灌山,乃闸山的一种,是专门为祈雨而举行的祭山活动,在旧时代大行其道,新中国成立后则销声匿迹。因此这一次灌山,好多程序都删繁就简,点到为止,据说只由天亮和另外一个人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净手焚香后,于苋麻沟取来一罐清水,罐在了闸山梁梁顶最中央的位置。另外几个人则隐身幕后,未曾露面。我后来一直怀疑棍叔也是这次灌山活动的人选之一,尽管他之前并不积极,后来也表现得若无其事。不过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一直不能肯定。曾经有一回我和棍叔闲话,期间几次欲以澄清,都是话到嘴边又不得不收了回来。其实有些话,不说比说了好。
说不上是灌山之后的第几天,一场突如其来夹杂着冰雹的倾盆大雨,把本来就因为干旱长得稀稀拉拉的庄稼,砸了个稀烂。那场雹雨的诡异让我无语。在我看来,它和灌山之间的关系更像巧合。但村民肯定不这样看。下这场雨的时候,我正放牛。我当时读初中,一放暑假就到队上放牛。那一天的雨下在午后,本来一直晴朗的天空,突然一下子就涌上了黑里透黄的浓云。我清楚地记得,云是从西北方向的天空中上来的,速度之快,令人措手不及,转眼就把太阳也包裹了个严严实实。我和牛刚刚走上闸山梁的梁顶,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就见棍叔在不远处一边喊一边示意我赶紧往回赶牛。棍叔之所以喊的同时还要挥舞着手示意,疑问是当时的风太大了,吹得连人都站不住,他担心我听不见他的喊声误事。棍叔的担心显然不是没有道理。事实是,我当时确实听到了棍叔的喊声,但棍叔的喊声是被狂风撕成碎片以后断断续续传到我的耳朵里的,而且声音模糊,要不是在特定的环境之中,几乎分辨不清他要你干什么。我赶紧把头牛折回,然后在空中摔几个响鞭。其实牛在很多时候比人还有灵性,大概也感觉到情况不妙,撒腿朝着回家的方向就一阵狂奔。这时天亮也和一群羊不知从什么地方风驰电掣般向着羊圈而来。在天亮和我相遇的那一刻,他除了让我动作快些,还用手指着天上,说连雨的声音都听见了。我以为天亮在作怪,谁知天亮一脸的认真,又一次用手指使劲向天上指了指。我于是停下脚步,竖起耳朵想听个究竟。果然,一片隐隐的波涛声,似乎包藏着巨大的不安,正弥漫在云层之中。我非常吃惊,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尽管我知道大雨来临的时候,能闻到雨的腥味,但能听见雨的声音,这还是头一回。然而我没有时间多想,紧赶慢赶刚刚把一群牛赶进牛圈的时候,一场夹杂着冰雹的瓢泼大雨尾随而至。那几乎是我见过的最凶险的一场大雹雨,只听见牛棚上瓦片破碎的声音,一片稀里哗啦,天像塌了一样。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雹雨才慢慢停下。
雹雨过后,大家发现受灾的只是本队的地面,隔壁队上的庄稼几乎秋毫无犯。其实这并不奇怪,常说过雨一走一条线,就是这个道理。
这一场雹雨带来的后果不言而喻,还没有来得及收割的粮食差不多完全绝产。接下来的日子要不是公家继续救济到年底,是没有办法度过的。我从小常听老人讲过民国十八年的大饥荒,饥饿的人们把草根吃光把树皮也吃光,最后只能易子而食。说实话,我觉得那样的事应该在故事中才会出现。哪知这一年我们这个队的人除了把地表能看得见的野菜吃得一棵不剩。不过,万幸的是由于每人每月有政府救济的二十斤高粱或红薯干做垫底,所以还没有发展到吃树皮的地步,后面的那一步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和本文毫不相干的事。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有一次我回老家,满山遍野的桃花正在盛开,却突然看见公路两旁高大的柳树齐刷刷全部被剥光了树皮。树虽然还没有被放倒,但裸露的白色树干和树头上刚刚展露出的鹅黄色树叶之间所形成的对比,触目惊心。那一刻,一种强烈的不适让我不能自拔。大概是为了拓宽道路,那些树后来被全部砍伐。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一想起这一幕,我仍然会产生一种绝望的情绪。
据说那些树都是左公柳,为当年左宗棠平定新疆时沿途所栽。
话说回来,遭了灾的人们心情不好是自然,不过带着不好的心情找到的原因也让人忍俊不禁。村子里很快就有了闲话,说几个捣蛋鬼不懂管子,把老天爷惹了。显然说的是灌山的事。别的我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一段日子棍叔和天亮好像有些灰溜溜的意思。这也是我疑心棍叔参与了灌山的理由。不过蹊跷的还有另一件事,那便是本该在雹雨来临之时挺身而出的铁将军,这一次居然也装聋作哑,一言没发。
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参加朋友母亲的葬礼,其间刻意约了同村一个发小一起回老家。之前我已经知道老家几乎走得不剩几个人了,一踏进村子,遍地的荒草和残垣断壁仍然使我感慨万千。大概是记忆中抹不去的有关灌山的是是非非,我们连想也没有想,就径直爬上闸山梁梁顶。坐在我曾经放过牛的山巅,俯视眼前一片废墟,不免有些伤感。那天,我们叙了很久,包括1973年的那场雹雨和之前灌山的事。直到太阳偏西才离开。临走,我们把手中还没有喝完的瓶装水倒在闸山梁梁顶最中心的位置,然后笑着说,我们也灌一下山,说不上过几天会下一场雨。我们所谓的灌山,不过是玩笑而已。谁知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这位发小突然打来了电话,说不得了了,昨天咱俩灌了山,今天老家一带就下了一场大雨,是巧合还是真有其事?我听了忙问是不是冰雹?对方说不是冰雹,是一般的过雨。我一听不是冰雹,才放下心来,便故意笑着说,哪有这样巧合的事情,肯定是昨天我们灌山的时候,感动了山神爷,今天他才用笤帚洒了一点雨。我记得大人说过,天上专门有一个管水的神仙,身旁有一个装满水的大缸。这神仙一年四季守着大缸,一旦人间需要雨水,他就用手里的一把笤帚蘸一点缸里的水,朝地面洒一洒。不过这位仙家有时候也会守着水缸打盹,拿天下事不当事,于是错过了雨季,结果闹得地面上苗枯叶黄,颗粒无收。显然,电话那头的同学有点兴奋,他和我一样,对这个故事再熟悉不过。不过一年四季守着水缸的神仙应该不是山神。山神的职责是看山守村,护佑一方百姓平安,如果只守着一缸水,显然无法交差。于是就有一个问题,闸山梁祭山明确祭的是山神,那么山神和这位有时候打盹的神仙是什么关系?如果关系摆不正,就算天上的神仙睁着眼睛,要不来雨也没有办法。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祭山神的地方在山顶,而山神庙却在闸山梁以下的地方。想想也是,除过山神,大多数神仙都在高处俯视人间,轻易不会委身平凡。祭山自然也要选在山顶,就算不是为了要照顾谁的情面,至少也能让山神和上方的神仙沟通起来直接方便。如若在山下,不免会被人间俗事烦扰,作为山神,起码在心情上就不会觉得自然。至于山神要把家安在山下,大概是为了方便平时访察民情吧。
四
老家原来的山神庙,在“文革”期间被拆毁,神仙也被赶出了庙院。大概是庙院空着也是空着,有人便在里面安了一个石碾,于是常常有人闲下来的时候,会“吱嘎嘎”推着石碾碾米。现在看到的山神庙,是上世纪80年代在原址上重修的。听人说这位山神在失去庙舍之后,被棍叔移到不远处的一个隐蔽的土龛中。不过这只是听说,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山神庙重修以后的第一个年三十,好多人都去抢头香,我也去了,却没有见到棍叔。重修山神庙,棍叔是倡导者之一,所以棍叔的缺位,让我有些奇怪。有一次棍叔来我家和父亲闲谈,我才知道棍叔并不主张到处上香求神。棍叔说敬神要心中有神,不然,香烧得越多,惹得鬼越多。时过境迁,现在再想起棍叔的这句话,竟觉得意味无穷。
重修以后的山神庙,很像一个平静的农家小院,每年寒暑假回家,我都会到小庙里转一转,感受一下似乎看起来超脱实际却充满了世俗意味的某种情绪。然而有一回,当我正站在庙院的当中看着正殿门上的一副对联的时候,却不料从身后大门的上方突然传来“哇呀”一声怪叫,我一时毛骨悚然,被惊出一身冷汗。转过身,才知道是一群乌鸦使然。退出小庙,我看见不远处的苋麻沟的沟沿上,乌鸦们起起落落。正是冬天,附近的田园被白雪覆盖,黑色的乌鸦落在上面,很像撒在宣纸上的墨点。我一时心驰神往,竟觉得那雪野以及雪野之上的乌鸦,可以随手卷起来带走。
棍叔看山的时候,遭遇乌鸦是经常的事。每当夏秋两季,作物成熟以后,乌鸦们就会不请自来,但棍叔顶多也就用手里的棒棒对着乌鸦们挥舞一阵,把它们赶走了事。我有时觉得乌鸦其实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对农作物会造成很大损害,尤其长在地里的庄稼,乌鸦们都有些敬而远之,是不是担心由于秸秆不能承受自身的重量,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庄稼之中而遭遇不测?不过庄稼一旦收割以后,它们就无所顾忌地把一片空地占满,然后一边小声叫着,一边放开肚皮啄食那些掉在地上的粮食。每当这个时候,巡山的棍叔就会绕道而行。事实上对于棍叔来说,这是一年当中最为清闲的一段时光。不要说乌鸦,就连天亮和他的一群羊,棍叔都不管。要在平时,棍叔比较担心的还是天亮赶着的那群羊。有好几次,由于天亮的三心二意,羊窜进了庄稼地,棍叔不得不赶着羊去找天亮。天亮看见棍叔会尽量显出知错改错的样子,但临了几乎都要皮笑肉不笑地说些阴阳怪气的话。棍叔几次扬起棒棒,结果每次天亮都佯装抱头鼠窜。棍叔只能绷起脸骂几句拉到。话要说回来,看山人和放羊的人本来就是天生的一对冤家,但棍叔和天亮之间并不是这样,虽然有时候偶尔会有一些小摩擦,然而这样的小摩擦,最后总是以喜剧的方式收场。
当一年很快就要结束的时候,闲下来的妇女们就背着背兜,拿着扫帚,先把树叶扫拢,再背回各自家中,留着冬天烧火做饭或者煨炕。男人们则把双手互相筒在袖筒里,要么闲转要么谝传,他们剩下的事情就是等着过年。这时还要继续忙活的人,只有天亮和棍叔。
秋天过去,冬天接着就来了。四五十年前的西海固地区,雪总会冷不丁提前到来,让还没有怎么做好准备的人们,有点手足无措。天亮照旧放羊。要不是天亮偶尔唱一两声,天亮的羊群和白雪混在一起,压根儿就看不清它们在什么地方。
棍叔则把一年来没有动过的钢凿和铁锤拿出来。钢凿需要打磨打磨,铁锤的锤把和锤头之间也必须再吃紧一些。在暖阳的照耀下,棍叔的准备工作做得一丝不苟。
生产队的时候,为了方便,差不多几户人家就有一合石磨,平时队里分了粮食,自己要吃的时候就抽时间自己推成面粉。推磨是非常枯燥的一件事,根据推磨的人的多少,有时可以用四根磨棍,有时可以用两个磨棍,最少的时候就只有一根磨棍。一般而言,一人抱一根磨棍,然后就在没有尽头的磨道里推着轰隆隆的石磨旋转。推磨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不要说不用脑子,就算想用脑子,推着推着,也会进入睡眠状态,所以只要有些力气,能抱住磨棍就行。由于要避开上工时间,推磨通常都是利用吃过晚饭以后或者天亮以前,这时走在黑洞洞的磨道里,人还会产生一种时空颠倒的幻觉。我几乎是从省事的时候就开始推磨,一年下来不知要在天昏地暗的磨道转多少转。当然,如果幸运一点,就可以从队上借一头驴来拉磨,但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在畜类当中,驴是非常老实的,只要用一块布蒙住它的双眼,它就绕着磨道一圈一圈往下走,不会怠工,也不会犯糊涂。我曾在一个老物件的展览会上见过一对草编的蒙眼,是专门给推磨的驴用的,活像现在的妇女用的乳罩,上面还用颜色染过。当时几个人讨论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用途,最后还是讲解员告诉的。可见农业文明的用心有多么精致,只不过我们很少琢磨而已。
尽管推磨对人是一种折磨,其实被折磨的还有貌似强大的石磨本身,经过说不清多少遍的互相研磨,两扇磨盘上的石齿到了年底就变得模糊不清,如果不用钢凿凿出来,接下来就无法磨面。所以差不多到了每年农历十月,棍叔就从村头到村尾,挨个儿凿磨。这时的棍叔戴着石头眼镜,躬身坐在磨盘上,双手握着铁锤,一锤一锤打凿石磨,直到磨齿清晰显露出来。凿成一合石磨,少说也得五六天,这样叮叮当当把全村的十几合石磨凿完,就进入了腊月。棍叔凿磨,只要管饭就行,不过每顿饭多少都得有几盅酒喝,除此而外,没有任何报酬。只要吃了饭喝了酒,棍叔就显得高兴无比。
接下来棍叔就要到脚户梁的尽头,去打扫一下一年来落在铁将军身上的硝烟和尘土。
这件事并不复杂,但需要细心。棍叔首先会认真检查一番铁将军是不是完好无损,如果有锈蚀的地方,他会不厌其烦地一点一点清理掉。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把铁将军的全身擦拭一遍,使它呈现出崭新的模样。如果有些地方用抹布不容易擦干净,棍叔就直接用手去擦。至于披在铁将军身上的那一袭红布,棍叔已经不止一次慨叹有些太旧了。但过去了一年又一年,棍叔仍然没有将那块红布换成新的,好在那块红布并没有破损,这让他稍微可以安心一些。每当这个时候,棍叔免不了会苦笑一声,他觉得相对而言,铁将军还要好一些,因为他棒棒和大多数人一样,穿在身上的衣服不仅陈旧不堪,而且破洞百出。这一切,棍叔不仅在心里念叨,往往忍不住还会从嘴上说出来,就像两个老朋友拉家常一样,棍叔要把自己心里的想法一五一十说给铁将军。除过铁将军,棍叔还必须把这孔狭小的窑洞再简单收拾一下,让它不显得散乱。我后来才知道,忙完了这些,棍叔并没有立即闲下来,他还牵挂着被赶出庙舍的山神。至于棍叔要做些什么,怎么做,什么时候去做,大多数人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对于棍叔的所作所为,似乎有人不以为然,但也有人坚定地站在棍叔一边。对此,棍叔似乎不十分在意,他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和他没有多大关系。倒是有人言之凿凿,说做梦梦见过山神,山神托他转告棍叔:棍叔的肉他吃了,棍叔的酒他也喝了。另外,好些年不见,山神也老了,头发白了,胡子白了,连走路都拄着一根棒棒。大家听了唏嘘不已,感叹之余,又有些不解,怎么连神仙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只是神仙的事没地方打听,慢慢地也就放在了脑后。
一座寂静的小山村,一切都按部就班,在寂静中有条不紊地进行。
虽然是穷光阴,但年的味道还是一天比一天浓了。所有的人都忙忙碌碌,尽管说起来免不了都要互相调侃在白忙乎。然而生活毕竟是生活,就算每天所打理的是鸡毛蒜皮,也是有价值的,更何况生活中的人们免不了还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些事情不一定都好,也不一定都坏,但由它们所编织的生活无疑是五彩缤纷的。
这其中有一件事值得一记:一年冬天,队长突然接到公社指示,要求家家户户过年期间必须在门前悬挂彩灯。我记得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显得非常兴奋,尤其是孩子们,个个奔走相告。然而高兴之余,大家却有些面露难色,因为几辈子都没有扎过彩灯,所以都不知道彩灯怎么扎。天亮想到了棍叔。棍叔虽然依旧没有喜形于色,但他很快就用竹子做骨架,用五颜六色的彩纸糊成了一个彩灯。不能说棍叔的彩灯糊得多好,也就是能看过眼而已。但他的做法具有示范效应,队上那些心灵手巧的年轻媳妇马上心领神会,于是第二批造型各异的彩灯糊了出来,惹得邻队的人都来参观取经,大家除了说灯笼扎得好,还说棍叔真是了不起,啥都会。我记得棍叔面对众人的恭维,终于没有抵挡住内心的喜悦所掀起的波澜,咧开嘴笑了一下。那是我印象中棍叔唯一笑过的一次。
那年春节,各家各户的门前无一例外都点起了彩灯,虽然各家各户要额外付出一些煤油的费用,但似乎没有人计较过。而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彩灯亮起来以后所带来的喜庆,真的感觉太好了。大概是意犹未尽,天亮居然用三个长长的木杆挑起三个彩灯,插在闸山梁的梁顶上,从山下望去,那三个灯笼就像三颗星星。
那些被星星点亮的夜晚,现在想起来,是多么的遥远。
五
大年三十的这天,棍叔还没有闲下来,他首先要早早地到大队小卖部里买几张红纸,然后按照自家门框的数目和每个门框的宽窄裁成对联的样式,再找来几个上小学的小辈将对联一副一副写就,这一年似乎也就真的收尾了。不过棍叔贴好对联以后,照例还要在山上转一圈。当然这一次巡山,完全是棍叔自己的决定,年年如此,雷打不动。
忘了是哪一年的三十,我和一群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实在闲得无事,突然心血来潮,决定要跟着棍叔到山上走一走,看一看。跟在棍叔的后边,我们就像一条尾巴,嘻嘻哈哈,左右摇摆。我们甚至看见在脚户梁的尽头,隐隐约约的天亮和他一群羊,如同一片云彩,从那座小山包上飘过,一起飘过的仿佛还有天亮那略带苦涩的歌谣。半个下午过去,快要落山的太阳正把万道霞光射向大地,就在这时,一大群乌鸦从闸山梁的背后起身,向着太阳的方向飞去。看着乌鸦一点一点沐浴在霞光之中,突然,原本还是黑色的它们,霎时变成了点点金光,仿佛要把豪华和富贵洒向人间。
我们激动不已,一阵狂呼夹杂着手舞足蹈,似乎也要飞了起来。
此时棍叔虽然也身披霞光,但对于我们爆发出的热情,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回应,这是一个几乎永远都保持沉默的人。至于他手中的棒棒,因为长年握在手上,早已经有了一层油光滑亮的包浆,在阳光的照耀下,看起来更像一件经年的装饰品。
虎西山,1961年生,宁夏隆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十月》《星星》《朔方》《绿风》等。出版诗集《远处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