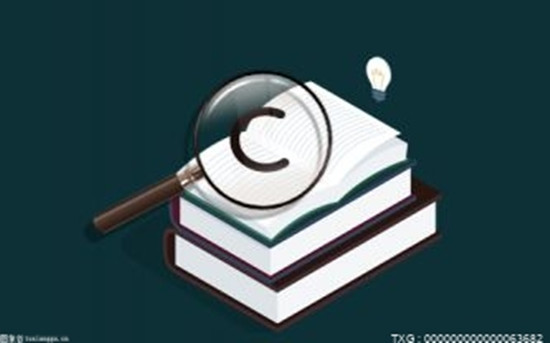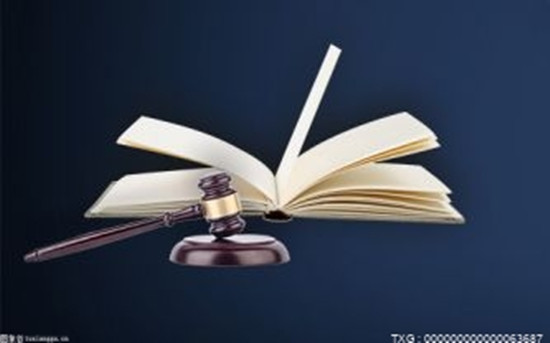离 骚(节选)
 (资料图)
(资料图)
战国·屈原
汩余若将不及兮,
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
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
长顑颔亦何伤。
掔木根以结茝兮,
贯薜荔之落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
索胡绳之纚纚。
朝发轫于苍梧兮,
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
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
望崦嵫而匆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朝发轫于天津兮,
夕余至乎西极。
忽吾行此流沙兮,
遵赤水而容与。
仆夫悲余马怀兮,
蜷局顾而不行。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离骚”写作年代,司马迁《报任安书》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汉人无异辞;但《史记》屈原列传又系于“(怀)王怒而疏屈平”之后。于是今人或认为作于见疏怀王时,或认为作于见放顷襄王时。有一种意见则认为屈原实际是两次被放,《离骚》当作于初放于怀王之后,似较能弥合旧说;同时要写出如此充实光辉的巨著,也确须兼有在政治生涯中经历了大的风雨,和在精神与体魄上有相当的余裕这样两个条件。
《离骚》与屈原政治生涯、战国时代风云密切相关,故全诗有极现实的思想内容和生活内容。但由于历史和艺术的原因,诗中又运用了大量超现实的语言意象、创作手法,把历史与神话、真实与想象奇特地揉合为一。它是如此华藻要妙,波谲云诡;如此惊采绝艳,炫惑眼目!以至读者只有紧紧把握住它的语义意象、历史内容及象征意蕴等诸多层面构成的审美结构关系,方能深入诗的意境而做到心领神会,而心荡神驰。
《离骚》既是一篇长篇政治抒情诗,又是一部伟大心灵的悲剧,全诗不带标点约2500字。它的篇章结构,可以看做由“述怀”、“追求”、“幻灭”三大部分组成的三部曲式的悲剧。在这诗剧的舞台上,自始至终活跃着一个英雄主角,那是诗人伟大人格的化身,全诗除了女须、灵氛、巫咸几个人物的对话,几乎全由这个主人公的活动与内心独白构成。
因为是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所以在以天下为己任的诗人笔下,才有如此使命感,紧迫感和危机感。诗中四言“恐”字,无非忧先天下之意。“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惟恐虚度年华,白首无成,遂朝于斯、夕于斯,深自勖励:“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不仅是一种情操与修养;揆之史实,则有“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怀)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本传)诗云:“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正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李白),充满自信,非徒作大言。
诗人在浪漫想象的境界中,开始了他那“气往轹古”的三次飞行。第一次飞行就从舜灵所在的苍梧出发:“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其目的是要由昆仑神山之悬圃,登上天庭,谒见天帝。从苍梧到悬圃,是一整日的飞行,诗人想在此“灵琐”小憩,无奈日色已暮。他不禁吁请和弭节,欲留驻飞光。此时离目的尚遥,然而诗人却表达了“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一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信念。
第二次飞行仍严格地以朝夕字样为标识:“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高丘无女即指高唐无神女,其寓意为楚国当局不得其人。这一部分的两次飞行,造境虽幻,结语却极现实。诗人在幻境中言路不通、障碍横生、六面碰壁的情形,实际上是他“以道诱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张惠言)的现实在梦里的投影。
如果说以上两次飞行均受阻于外力,终至失败的话;那么这第三次经预言家肯定为吉祥的飞行,则由于内因,最后半途而废,未能实行。但这次朝发天津、夕至西极的行程是修远多艰的,付出的努力极大,场面也空前热烈。当其西行左转,胜境在即的时候,他自己忽又恋眷旧乡,改变主意,对先时取向作了坚决否定。这出乎意外,又合其初衷。“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样,对诗人来说离开楚国寻求发展的任何意向都是“此路不通”,而在楚国又没有“足以为美政”的可能,于是在全诗的尾声中,他宣告了理想彻底的幻灭并准备用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
《离骚》有如一部大型交响乐,它的情感内容丰富、复杂、矛盾而又统一。其中最突出的情调是深切的乡土之爱,及植根其上的爱国主义激情。诗人被楚国遗弃,然而“落红不是无情物”,他本人却无法离弃他的故土。所以有人认为抒情主人公人格结构的核心就是对祖国的苦恋。这在士无祖国的战国时代,是一个特例,而对后世的民族英雄则是一个楷模。
文 / 周啸天
视频、文章版权归“啸天说诗”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