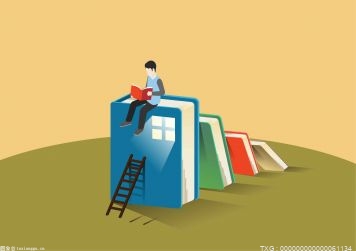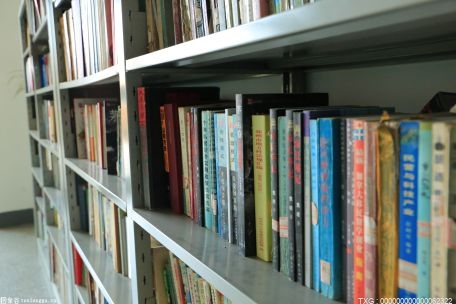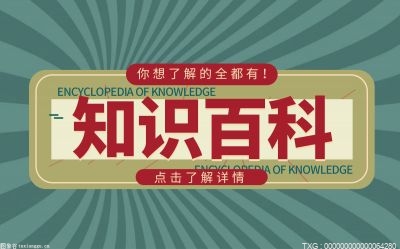这也太意外,太突兀了吧?“磨剪子来----戗菜刀”,这久违了的吆喝声,如今竟又从古城西安社区间,那鳞次栉比的楼宇拐角里,偶尔传出来。它既熟悉又陌生,既遥远又亲近,一下子唤起了五十年代期间,我年少时的多少回忆哟!
那时,在西安古城的大街小巷里,经常会见到,有一些身怀技艺的民间工匠,他们带着各自简单的工具,或挑担,或背驮,或腰挎,或推车,走街串巷,凭着各自一门灵巧的手艺讨生活。他们所施展的这些人工技艺,与那时西安城人日常生活的需求,贴得是那样地紧密,以至于这些手艺营生的本身,也成了古城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了。
比如,谁家的水缸冻裂了,有锔缸的;谁家烧火的风箱漏风了,有勒风箱的;谁家的水桶掉到井里了,有捞井的;谁家的顶棚破了,有糊顶棚的;还有什么钉盘子钉碗的,打竹帘子的,补竹席子的,修笼屉的等等,可谓五花八门,令你眼花缭乱。所有这些,连同那些走街串巷,花样繁多,听起来就让人垂涎欲滴的近百种民间小吃,连同古城里敦厚淳朴的民风,以及洋溢在大街小巷里,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一起,俨然绘成了一幅西安城恬淡自然的坊间风情图。
 (资料图)
(资料图)
这里每一种手工技艺,都有别样的精彩,都有不同的吆喝声。有的即使是不吆喝,也有他们各自特殊的传递讯息的门道路数,让你老远一听,就知道是做什么的来了。例如,锔缸的是敲一节竹筒,“帮帮---帮帮”,声音清脆响亮,就像是傣族人跳竹竿舞时的敲击声。
打竹帘子的就更简便了,肩上扛着一条长而窄的板凳,一只手再拿着干活时坐的小木凳,一边走一边相互敲着,发出“砰---砰砰”的响声,有点儿像戏台上敲边鼓的声音,极富节奏感,煞是好听。
修蒸笼屉的一般不吆喝,推着一副木箍独轮车,因为这种木箍独轮车推起来,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巷子里的人老远就能听见。在竖起来的车框上,一边挂满了预制的木质薄型圈料,一边放着各式大小不一的工具,最特殊也最不可或缺的,是车框上还缠绕着用牛筋制作的紧固带,因为缝合固定笼屉,以及支撑屉骨时,必须用得上它。而最重要又最显眼的一件工具,便是那一把轻便简易的手动摇臂钻。如今,这种手动摇臂钻,恐怕只有在偏远的乡村,或者更遥远的山区林区也许还找得见了。
那时,每一种游走于坊间巷里的手工技艺人,当他们在施展技艺的时候,都会令我感到新鲜好奇。我往往会安静地守在一旁,双手稳稳地托住两腮,瞪大了眼睛,聚精会神地欣赏着。现在再闭上眼睛回忆起来,那情景就像一幕幕活报剧,会立刻浮现在我脑海里。它们是那样亲切而熟悉,又是那样陌生而遥远。
最有趣的要算那捞井的了。他往往备有一套狗皮的翻毛短褂,以及过膝长的狗毛皮裤和橡胶套鞋。手里提着那头部有多个分岔的铁钩,西安人叫它“捏钩”。肩上扛着一根长长的带铁钩的竹竿,杆子上套着缠绕成环形的牛皮拧成的绳子,老远看上去,就像刚从秦岭山里出来的猎人,引得巷子里的小孩子们,惊异的眼光会齐刷刷的向他投去。
若被谁家请去捞井,到了井口,他会先向井里投一块小石子,侧耳听辨一下井深和水深。若是都较浅,他便用带钩的竹竿直接捞钩。若是遇上井太深或水太深,那也难不倒他。他会向院子里的人家借两块小镜子,一块摆成大约45度放在井口边,另一块放在有太阳光的地方,调整好镜面,好让光线经过折射照到井里。下井前先把狗皮衣裤穿戴齐了,再喝上几口烧酒,以抵御井内的寒气。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沿着湿滑的井壁上浅浅的脚窝,一步步地蹭着下去。估计差不多快到井底了,再用牛皮绳子拴着的铁钩,去仔细地寻找钩捞。等钩子已牢牢地钩住了水桶,他便又顺着脚窝爬上来,再把牛皮绳子缓缓提上井台。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捞井人每次下井前,总不忘先向井台神龛里的龙王爷牌位跪拜,以祈求保佑。等捞上了水桶,上井来第一件事就是向龙王爷磕头谢恩。
如今,这些世世代代师徒相传,口手授受的民间手工技艺和行当,都逐渐被现代文明淹没或淘汰了。生活中你所用得着的各种各样的服务,也的确是越来越便捷和高效了。然而,再静静地想一想,在我们为此而庆幸的同时,是否也会有一丝丝的惆怅或失落?因为,那些伴随着恬淡,伴随着温馨,伴随着亲近感的坊间风情也都随之消失殆尽了。
窗外,“磨剪子来----戗菜刀”的吆喝声,在熙熙攘攘的纷乱里,有时竟还能隐隐听得到,这莫非是在梦境里吗?
相关链接:
朱文杰:西安老街巷里的吆喝声
记忆深处:西安小巷中的河南人的吆喝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