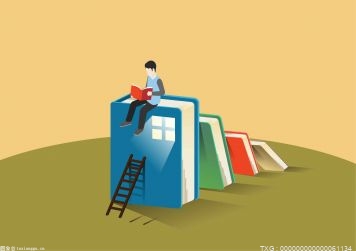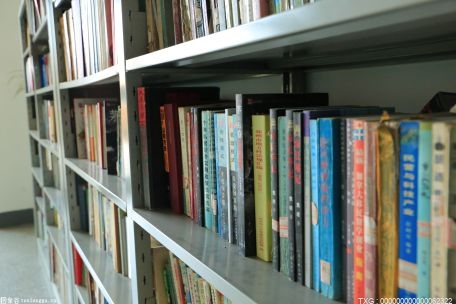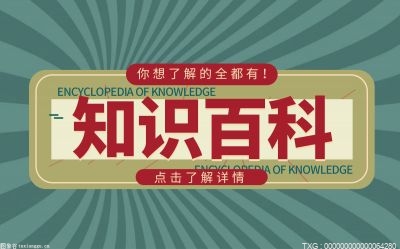為文學愛好者引路,為文學寫作者服務
/十一月“小城记”主题征文评选活动/
初选合格作品展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作者简介:赵俊松,四川省南边文化艺术馆2022届签约作者。
创作手记:童年的小城田园生活是我收获非常巨大的一段时期,在没有电子产品干扰的生活里,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去亲近自然,感悟自然。这段珍贵的童年生活留给我的是丰厚的情感底蕴和无限的思想启迪,相信这就是大自然以独特的方式给予孤独童年的我的一份礼物吧。
小城的田园
21世纪初的偏远小城,还随处可见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在没有车水马龙和高楼耸立的年代,深山老林和贫穷就是外乡客人留给小城最多的评价。近些年来,学业与疫情的交织让我少了许多和故乡的联系,但是每当闲暇游玩客乡的田园,小城故乡的山水却仿佛变得格外清晰。
童年的故乡是与信息化时代隔绝的,在那个年代里,夏日里远行的客人会用火把赶路,星空下的田野比诗篇更优美。淳朴的老农白天也许还在为地界的划分吵得不可开交,但当夜幕降临,万事也便归于祥和,大院的地坝便是大家促膝闲谈的专场。
童年的我是和祖父祖母一起在小城里长大的。祖父祖母喜欢在田间地头忙着各自的活计,由于担心我一人在家没有玩伴,所以也会常常把我带在身边,穿梭在田间地里。祖父往往担着粪桶走在最前面,祖母会扛着锄头走在中间,我也模仿着祖母的模样扛着专属于自己的小锄头悠闲的走在后面。小锄头是摆设用的,祖母怕我出门没有东西拿在手里会到处跑,所以让街上的铁匠师傅给我打造了一把,据说还花费了他不少精力。祖父大抵是瞧不上我翻土的,他总认为我翻得太浅,还会把我翻过的土又翻一遍。小时候的我心里也藏着满满的傲气,祖父瞧不上,我也不会讨好他做个乖孩子。
小城的田野是美食的田野。世纪之交的农村还有大量农民喂养蚕子,桑树在田间地头是不难看见的。晚春初夏之交的桑树上紫红相接,桑葚对于农家孩童来说真的并不稀奇。初夏时节,山野的刺果用金色宣示着它的到来,刺果甜甜的外表下其实藏着酸酸的内心,一粒一粒吃下去是不过瘾的。若当刺果的酸甜熟悉了孩子的味蕾,那么盛夏也就悄悄来了。乡野的盛夏终究是要比城里清凉许多的,这一点可以从正午还在田垄上除草的老农身上可见。秋天是祖父祖母的收获的季节,夏天则是我收获的季节。夏日的傍晚天空泛着霞光,太阳在山间徘徊中缓缓落下,童年的我总会在夕阳西下时拿着比自己还高的竹竿穿梭在树林之间,寻找着那份属于自己的收成。蝉壳——一种常见的中药材,也是我盛夏里搜寻的目标。蝉喜欢在夏日夜晚湿润的土壤中破土而出,然后在太阳出来前爬到高高的树干上,迎着烈日而鸣,在秋风萧瑟中骄傲退场。蝉壳捡累了,可以到山腰的草丛中寻找另一种果实——地果。地果也是酸甜的,和草莓有着相似的地方,这种野果喜欢藏在藤蔓里,一般很难发现它。不过对于农家的孩子,识破这些伪装自然不在话下。
小城的田野是诗意的田野。晚夏的日光已不如盛夏时那般毒辣,老农们为了抓住夏日的尾巴晾晒粮食,总会算着日子收割田间的稻谷。在农业机器还没有传入小城的年代里,一个打斗,一个打席,一张围布就是收获粮食的设备。由于那个时代不用依着收割机的进度,所以有经验的农家会待到稻谷完全金光了再去收割。金光的稻谷远远望去似乎与晚霞相接,不知是晚霞渲染了稻谷,还是稻谷涂鸦了晚霞。当天边只剩下一抹晚霞的亮色,忙碌了一天后的归家老农也为这静美的山间增添了一份灵动的墨画。
故乡的小城里留着童年,少年时太多的美好,小城的四季里有写不完的绝美文章。常常遗憾自己庸俗的文笔,不能将那山河的壮美铭刻在云肪之上。
由读者进行中肯的评论点评
终审环节
依据作品质量选出优秀作品
获奖福利
复选合格作品:在南边文艺网专栏全文刊登;
寄发稿酬并颁发专栏用稿通知;
终选优秀作品:颁发获奖证书;
择优发表在《文华报》。
编辑|何蕊芮
主编|彭旭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