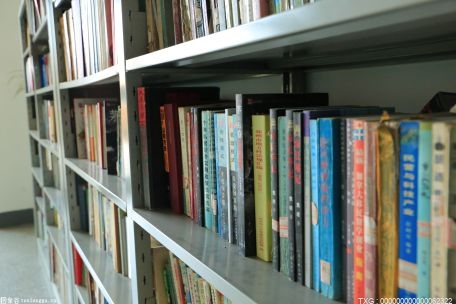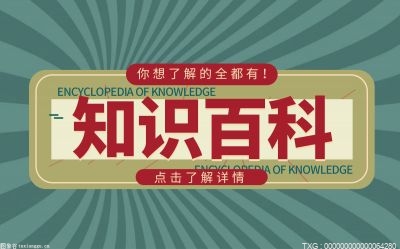羊城晚报《客家文脉》11月17日版面图
雨中程江河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詹苇丽
出门的时候,天还未全黑,空中洋洋洒洒着微微的细雨,偶有三几个黑影从半空中掠过,那是晚归的鸟儿。我想许是雨天鸟儿难以觅食,它们便回得晚了。
这是秋日一个黄昏,我应友人邀请到程江河畔不远处的饭店晚餐,出来的时候已经暮色四合,掺杂着丝丝缕缕、若有若无的细雨。我忽然有了雨中漫步的雅兴,于是向店家借了两把伞,拉上友人便出门了。
信步微雨中,人行道上的紫荆花落英缤纷,飞鸟与落英让我不可避免地想起晏几道的那一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年轻的时候,我每每念起这句,心中便有万千感慨。在生活中,我们何尝不想成为微雨中的双燕,却不留神在岁月的变迁中成了落花人,遗世独立于风霜雪雨之中。朦朦胧胧的雨幕中,雨点轻轻打在伞面上,像俏皮可爱的小精灵们偷偷地踮着舞步,又像静夜里情人们的呢喃细语,缠绵悱恻、缱绻温柔。友人紧紧相随,她深谙我的习性,只默默地陪伴一侧,我们并肩静静地走着。
暮色微雨中,远山影影绰绰,程江河的水在不远处悠然流淌。都说山因水而灵动,水因山而秀美,在客家大地上经年流淌的程江河,据说也历经了岁月的风风雨雨,即使在最艰苦的岁月中,仍不忘恩泽一方百姓,养育一方水土。我还记得好多年前友人也曾带我来过此地,那时候程江河畔还是荒野残地,如今放眼望去,两岸灯火辉煌、璀璨一片。此时道路两旁的路灯已经悉数亮起,照耀着被细雨冲刷得晶莹透亮的翠碧色树叶,白日里忙碌的时光也在此刻变得安静闲适。河畔的芳草地上盛开着五颜六色的格桑花,细细密密的雨中气定神闲地轻歌曼舞着,映衬着身后的雕栏玉砌。绿色的叶子和五彩的花朵,让眼前的程江河夜色幻化成一首流行风格的民谣,让人心神荡漾又暗生欢喜。
走到河畔岸边宽敞的人行道,我们驻足靠在仿古河栏边。雨仍细细密密,近处的水、远处的山都在夜色中成了一幅迷蒙而多情的水墨画,此时的程江河,触目皆是美景。正沉浸其中,雨突然大了起来。豆大的雨点紧锣密鼓地敲在伞上,身外的河面已然烟雨蒙蒙;远处岸边的霓虹灯光闪闪烁烁投射在河面。
静静地伫立在雨中,我感觉灵魂似乎已经被带到咫尺之外的河面之上。那无法言述的流光溢彩,又让我情不自禁地怀疑自己穿越到了十里秦淮,繁华梦中烟笼春水盈如玉;又无端念起柳永的那一首千古流传的《雨霖铃》: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吱嘎”雨中忽然传来一声刺耳的急刹车,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的道路上,一辆小货车打着双闪灯停在了路边。小货车前面有一辆电动摩托车横在路边,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伯坐在车旁的地上。我和友人第一反应是出了车祸,连忙跑过去。小货车司机是个年轻小伙,憨厚的脸上挂着焦急的表情。我们走上前的时候,他正蹲在老伯前面温声问询情况。我们才知道眼前一幕并非车祸,而是老伯骑着车忽然身体不适,摔到路边,恰巧被热心的司机小伙看到,停下来施以援手。我们帮忙打了120,司机小伙又帮忙将电动车推到人行道上的停车处锁好。
目送救护车和小货车远去,我和友人继续慢慢地走着。看雨落在河上烟波浩渺,看雨落在灯下的叶子如珠玉滚落,看雨落在花树上,一树的落英缤纷,看雨落在洁净路面上,溅起一朵朵银色水花儿,眼前的世界通透明亮而美好……一路雨大了又小了、小了又大了,天籁之音尽在耳边,程江河的绝色佳境尽收眼底,雨声相伴美景相随。
雨中漫步,无意间邂逅一份浪漫情怀;自然的和谐、人的和谐,在微微雨中,更是让程江河美成一幅画。
梅县新城 叶海威 摄
客家民歌趣谈
□黄育培
一
民歌来自生活,为人们喜闻乐见,为生活添姿添彩,为民间文艺传承发展推波助澜。世界各国有不同风格的民歌,我国各民族亦有不同凡响的民歌。梅州的优秀民歌作品在报刊登载,歌曲在电视、网络传播。因其主题鲜明、风情浓郁,自然而然走到人们的心里来。
梅州客家民歌从大迁徙一路走来,有山歌、情歌、童谣、梅水歌谣、竹板歌、三句半等,传承千年,丰富多彩。新中国成立以后,优秀民歌见诸报端或书籍,或打造成歌舞形式。20世纪下半叶,山歌剧出现,在城里乡间演出,在舞台荧屏展示,走向大城市,走向国外。
客家民歌以山歌为主,各地山歌有不同特色。因为松口古镇、历史文化名城梅城的山歌源远流长,梅县被称为山歌之乡,人们皆耳熟能详来几句。近年来,客家山歌走向世界,梅县民歌演唱出现在央视、出现在东南亚各国。
21世纪以来,客家民歌创新发展,脍炙人口的佳作层出不穷,民歌新秀不断涌现。民歌演唱及歌舞在灯光、音响、舞美效果下,惊艳了所到之处,解馋了民歌迷和客家游子。
二
民歌起源于生产劳动、感情交流、节日娱乐以及启蒙教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广为流传。
客家民歌的起源应追溯至千年前。因战乱或自然灾害,形成史上中原大迁徙,形成客家人和客家文化。人们依山傍水建立村庄,耕读生活,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民歌成为心灵慰藉、快乐源泉。客家民歌贴近生活,涵盖节日喜庆、男女爱恋等方面。
山歌在客家民间普遍流传,其赋比兴手法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被学者称为“古代文化的活化石”。诗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山歌的“一条花树路边生,花又红来叶又青;晤知阿妹哪名姓?手攀花树问花名”,其素描、双关、比喻何其相似。“春到人间百花开,一枝红杏出墙来;心想上前摘一朵,新打剪刀口难开”,这些山歌的描写生动传神,类似技巧比比皆是。
梅水歌谣与竹枝词相似,贴切、生动、感人。据传,20世纪上半叶因战乱,曾有外地富庶人家及年轻女子来梅城避难,有些成为歌女。傍晚,梅江、程江交汇处的老百花洲榕树头小船云集。曾有梅水歌谣写道:“百花洲头水悠悠,佳人公子放艇游;半夜歌声犹未竭,琵琶弹破一江秋。”这是多么生动的写照。梅水歌谣风行至新中国成立之初,此后逐渐与山歌融合化为风格独特的新民歌,多数一题数节,因其主题鲜明、名家演唱而流传。
三句半风趣幽默,笑里藏机,或带讽刺意味。曾盛行于20世纪上半叶,此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颇为活跃。据传,梅县曾有个男孩因为交不起学费,母亲教他找到当军官的舅舅那里。舅舅知其来意,对他说必须拿出才学,哪有白得钱财的?这男孩想了想,说:“我会三句半。”舅舅应允其“真感情”才算数。因见舅舅打仗瞎了一只眼,他漫步吟道:“出门在外乡,见舅如见娘;两人同落泪——三行!”情真意切却令舅舅哭笑不得,只好打赏他。三句半多为七字一句,第四句画龙点睛两至三个字。这种幽默的形式已经很少出现了。
流传甚广的竹板歌依然活跃,而且有传承人。历史上曾称它“五句板”“叫花歌”,一是歌者以竹板为节奏,二是曾为乞讨之人的歌。竹板歌的另一独特之处是传本说唱。民间故事经艺人说唱,感人至深。20世纪中期,竹板歌说唱颇受欢迎。歌者走村串户,在晚上应邀说唱;亦有专业艺人在舞台表演。它以竹板为道具,开场歌词大致是:“竹板一打闹洋洋,五句歌子就开场。善恶有报说故事,人间传奇天下扬,先生女士听分相。” 竹板歌演唱活跃至今,而今杯花舞则瓷杯声声,应是竹板节奏的创新发展吧。
童谣一直是客家启蒙教育形式之一。“月光光,秀才娘,骑白马,过莲塘!”形象生动,令人终生牢记。在创新发展中,童真童趣的童谣更加优美,更为儿童喜爱。每年暑假,各地都在组织童谣比赛,现代版的原创新童谣渐渐成了主角。
三
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工作中,梅州客家山歌成为国家级“非遗”,梅县松口山歌则是省级“非遗”……
松口山歌中外闻名,山歌故事特别优美。松口山歌源于赵佗的三万驻军、五千箕妇驻扎在松口,为安抚军心,松口古镇街边、码头便设有对歌台。月夜对歌,情侣款款,历史造就了松口古镇的百家姓。古代对歌以生活情趣及爱恋为主,为山歌奠定基础,因而松口山歌声名远播。
20世纪60年代,山歌题材电影《刘三姐》风靡国内外。主演黄婉秋祖籍为梅县,她曾于改革开放之初回来寻根问祖。据传,《刘三姐》的原型刘三妹曾与秀才在松口古码头对歌,“自古山歌松(从)口出,哪有山歌船载来?”如今,松口的中秋便是其山歌节,中山公园、古街头依然在对歌,风情依旧。
有史以来,梅城文人云集,文艺长盛不衰,民歌极其活跃。梅县民歌史里,历史文化名人黄遵宪的山歌也写得极好,如“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因为分梨故亲切,谁知亲切转伤梨(离)”,是生活中的生动写照。
这些年,梅州常见有别于山歌和古诗的新民歌。新民歌主题鲜明、意境优美、韵味十足,生活气息浓郁,经文艺家谱曲演唱,载歌载舞,令人耳目一新。在文艺创新发展的时代,新民歌正在形成文艺新潮,闪亮前行。
客家大盆菜
□黄颖
客家大盆菜(俗称盆菜),旧时为富裕人家的新年佳肴,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春节团聚,一道吉祥寓意、和谐团圆氛围的大盆菜,是一场客家视觉盛宴。
所谓盆菜,是将食材分层汇聚一盆,象征“盆满钵满”“团圆美满”的特色菜式。上好食材,层层相叠;山珍海味,喜从心生。盆菜体现其味道精髓,浓郁滋补,汤汁鲜美。未吃先闻香,然后分层揭晓,情趣盎然而吃。其实,大盆菜由来已久,亦称为大盘菜。千年以前,交通不便,生活艰难,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时停时走,有分有合,大年三十则必须赶回家与父母团聚。常常是人齐菜凉,于是做成大汇聚的保温盆菜。据传,古时大盆菜用木盆或木桶清蒸,共分三层,第一层肉、第二层素菜、第三层炒面。其福气满满,因而得以流传。
客家人南迁定居以后,过着山村耕读生活。男人必须出门挣钱,寻求仕途或经商。生活慢慢稳定了,过年风俗却没有变,而大盆菜却随环境而变通,随南方食材丰富多彩而安排。第一层铺满农家肉类;第二层摆放素菜;第三层因南方缺少面粉而改成米粉丝,或香韧的米粄。猛火加热后文火慢蒸,第一层的肉汁稍带香味向下流,下层的素菜吸纳肉香,融合的佳肴味道在风中弥漫,欢乐喜庆。后来,小型家庭将大木盆改为较小的瓦盆。但是,不管何种食材,盆菜的制作都是将丰富的食材叠进盆里,易吸收肴汁的素菜放在下面,汁液交融,渐入佳境。如此融合的特有滋味,为家庭团聚带来欢乐氛围。
每逢新年或喜事,尤其是外出经商的游子归来团聚,客家人会在自家屋内摆盆菜宴,有着五谷丰登、经商发财盆满钵满的寓意。盆菜在形成一道客家名菜中,带着祝福的意识,带着美好的愿望,带着文化的内涵。
两年前,我在一家餐饮连锁公司工作,对盆菜进行设计,强调挑选绿色新鲜食材。菜式举例如下:
其一,乡村大盆菜。设计为三层,第一层有白切鸡、卤鸭、红焖肉、肉圆,淡水大虾;第二层有香芋、金瓜、冬笋、玉米、香菇、炸豆腐;第三层有粉丝、面粄。该款盆菜适合家庭团聚,可供5至8人享用。
其二,海鲜大盆菜。设计为四层,第一层有九节虾、深海鲜鲍鱼、小花胶、海参、鱿鱼、瑶柱;第二层有白切鸡、卤鸭、烧乳鸽、牛筋丸;第三层有香芋、金瓜、冬笋、花菇、玉米;第四层为薯粉丝。该款盆菜适合亲友团聚,可供10至16人享用。
如今,茶香酒香,菜盘子、果篮子丰富多彩。寓意团圆美满的客家大盆菜,定然给你其乐融融的视觉和味觉盛宴。
山乡行
□罗琼
老街晨曲
临街旧屋,檐下的蛛网在晨风中飘荡,细小的露珠折射出秋阳的明媚。
猪肉档、早餐店是山乡墟市最早醒来的一拨,清晨宁静的老街从这里慢慢变得热闹起来。窄小的街道两旁摆卖众多客家山乡的土特产,芋头梗、狗爪豆、苦麦皮、笋丝干……那是大自然对这方水土的馈赠。
竹匾里装着的各种小食更是吸引着游人的眼球和味蕾,盐水粄、芋粄、粟米粄、发酵粄、“老鼠”粄……甜的、咸的、淡的、放姜汁的,原汁原味,无比诱人。那是山乡人智慧结晶创造出来的、属于客家古镇的独特味道。
勤劳的人们起个大早,一边与熟悉的档主拉拉家常,一边把最心仪的肉蛋果蔬仔细挑选带回家,烹制一家人香甜富足的幸福日子。
乡野秋色
深秋,季节走近寒露。在客家小镇,你几乎难以看到枯萎干燥,万物萧瑟的现象。因为在这里,有漫山遍野的青青翠竹。那延绵数公里、源源不断为当地奉献美丽与财富的竹子,已成为“竹乡”的无声广告。
四季之中,我喜欢盛夏的清凉,更爱多彩的金秋。这个季节,除了充满生机的绿,还有稻谷的金黄。田野里、山崖边,野葛藤开出紫色的花,一串串一嘟嘟,枫树们举着手掌般的叶子,开始慢慢变红了……
“秋日胜春朝”,这些颜色在蓝天白云下,显得多么自然与和谐。蜿蜒在青山绿水中的小河,时而平静如镜,时而急涌奔流,像一条系在仙女腰间的玉带,那幽深的绿,和着两岸的旖旎风光,让人醉在梦境中。
松源镇桥背村探秘
□温丽容
松源镇桥背村地处梅州市梅县区东北部,是曾被海外誉为“商王”的刘佛良故里。假日里,我骑摩托车前往该村一探其风采。
山道弯弯,风光无限,目不暇接,且行且停。来到桥背村的门户——人称“小三峡”的口缺峰,站立聚奎桥中央,凭栏窥探,只见桥面到峰底的几十米落差似百丈深渊。顿时,惊恐心头起,寒战脚底升;虽七月盛夏,竟冷汗涔涔。
聚奎桥未建造以前,口缺峰峡谷横陈,交通甚为不便。虽曾有小舟摆渡,奈何年年雨季降临,河水湍急,凶险万分,两岸隔绝,望河兴叹。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由本乡人募资兴建石拱桥,取名“聚奎桥”。从此,峭壁峡谷间,一桥跨南北,两岸变通途。经风历雨两个多世纪,至今仍巍然屹立,客家智慧与工匠精神可见一斑。
口缺峰峡谷长约数百米,两岸悬崖峭壁怪石嶙峋,河水清澈鱼翔浅底,竹尾潇潇林木森森,芦花摇曳白鹭翩跹。桥尾侧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径,似羊肠蜿蜒而下,消失于神秘的谷底。不知深谷之下会是怎样的世界?霎时浮想联翩,脑海里倏然闪过《桃花源记》:“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此刻涉险趋水,可有另一世外桃源之遇乎?
溯河而上乃是桥背码头,有点像松口的火船码头。沿台阶拾级而登,眼前豁然开朗。举目顾盼,古民居比比皆是:奉政第、将军第、南欣楼、明远堂等错落有致,各领风骚。伫立良久,环视这不足千人的小村落,依山傍水,绿满田畴,竹篱茅舍,曲径通幽。高处有一株二百多年的古榕,撑开巨大的伞盖,蓊郁茂盛,仿若百鸟天堂。“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不就是眼前这桥背村的样貌么?一时间竟犯起难来,不知该取径西东。我哑然一笑:何必煞费苦心,跟着感觉走,山重水复之境必有柳暗花明之奇。
河道旁与将军第紧密相连处,竟藏有一美妙之所——白墙黑瓦的“竹兰书馆”,几杆修竹旁枝逸出,石阶之下流水淙淙,整个就是一幅淡雅素描,透释着天然简洁的幽兰之气。想想当年那不知名的馆主栖息于此,临水畔相约三两知己,清风明月,河水渔火,把盏论文,闲话农桑,一如“共剪西窗烛”之妙境!
慕名寻访的明远堂静卧在茂密的树林下,至跟前才发现,一副铁将军将来客拒之门外,沉默的大门紧闭,仿如时间老人黝黑的背脊。好可惜呀!无奈何转身作别,身后落下串串不舍和遗憾!行至村前复回首遥望,六纵三横两层的明远堂好似一幅铺开的水墨丹青,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筑室百堵,西南其户”莫非指的就是这偌大的建筑么?
传闻明远堂拢总大小118间房,屋主何许人也,竟有这等魄力和财力?其非外人也,他就是生于此桥背村的传奇人物——刘佛良。
自古以来鼎鼎大名的富商不乏其人,名满天下自不足为奇。可是,从客家小山村里走出去的刘佛良,竟能赢得“夏威夷商王”的美誉,则委实匪夷所思!
据记载:刘佛良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卒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享年78岁。早年家境清贫,9岁即随父街头卖艺,放过牛、耕过田、也曾挑担度日。清光绪二年(1876年),20岁的刘佛良漂洋过海,到夏威夷当契约工,此后开始从商,生意越做越大,逐渐遍及美国夏威夷和中国香港、上海、广州、汕头等地。刘佛良成为富商后,始终不忘根系中国,毕生爱国爱乡。辛亥革命时期,捐巨款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开展反清斗争;中华民国成立后,又响应“实业救国”号召,投资兴建粤汉铁路、潮汕铁路和兴办上海中国银行。刘佛良情牵故里,好善乐施,赈济乡民,建桥修路,仅在松源镇就捐建了8座石桥,乡里民间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刘佛良的趣闻轶事。
看了刘佛良的故事,心底下那曾经纳闷桥背村何来这样美轮美奂的民居之谜,已显露端倪。
兜转之间,来到桥下街。这是桥背村通往口缺峰凹下码头的必经村道。曾经的桥下街,是下南洋的歇脚站,还有旅馆、商行等。老一辈曾说“未有松源圩,先有桥下街”,可见桥下街对松源的经济发展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踏进鹅卵石铺就的狭长街道,山外来客绝难想到,在此“穷山僻壤”的山村里,竟然楼宇并立,形态各异。尤其是还有南洋风格的三层骑楼,如此规模令人不敢小觑。细看墙上的彩绘色彩依然,虫鱼鸟兽浮雕清晰可见。令人惋惜的是,大多建筑岌岌可危。近年来,松源镇和桥背村致力于抢救保护,临街的“联益书社”就已经重新修葺。别小看了这小小的书社,它在松源革命队伍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站在“联益书社”旧址前,看着斜阳透射下的木质窗棂和楼梯,光影斑驳,有一种梦回烽烟时代的错觉。
游桥背村犹如走入一座自然与文化交融的博览馆,不止有优美险峻的口缺峰,有完整的古民居建筑群,有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更有记录红色故事的原址,更有极富传奇色彩的人文故事。这个美丽的小村庄如今迎来更大的机遇,正在建设的省道223线如火如荼,宛如巨龙,将从桥背村穿行而过……
倘若昔日“商王”魂归故里,想必会感慨万千:物换星移,沧海桑田,祖国强盛。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朱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