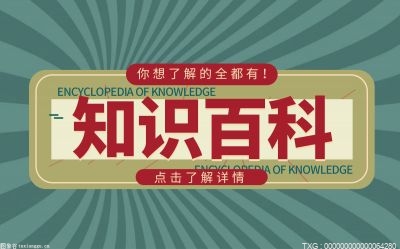民国早已远去,但独属于它的魅力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张恨水、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这些早已与时光长河融为一体却始终活跃于后人记忆中的先生们,在各自的婚恋生活中经历的阵痛与蜕变,始终与其创作相联结。读懂他们的婚恋历史,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幕后的创作,进而更深刻地领悟爱情与婚姻,了解婚恋观变迁在历史洪流中的作用。
团结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夜沉月碧落:多元婚恋形式中的民国作家——中国现代作家的蜕变一代》一书,选取部分民国知名作家,在叙述他们婚恋历程的基础上,结合他们的创作生涯对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婚恋模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引发了对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婚姻困局”现象的思考。
正所谓,“夜已深沉,心上月高悬碧落”。让我们跟随《夜沉月碧落:多元婚恋形式中的民国作家——中国现代作家的蜕变一代》,一起走近这些知名作家或美满、或坎坷的情感世界,从文字与故事中透视20世纪婚姻观念变迁及其历史影响。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近代婚恋观的变迁
20世纪初期,受时代转型的影响,中国人的婚恋观发生巨变:几千年来的包办婚姻观念逐渐被打破,而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主张,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接受。
或许因袭过重,晚清以来流行的仪式化婚姻观念,注重家族血脉和子嗣延续,强调家庭责任的婚姻形式,仍大行其道。这种规范外在行为的婚恋观,推崇夫妻间的责任和彼此间的敬重,引领时代风尚的作家、诗人和学者对此也难以幸免。
然而,这些身处时代潮流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毕竟沐浴在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时代风气下,自然不会甘心谨遵父母之命、在压抑的包办婚姻中屈服,他们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抗争。
有的作家基于人性的良善和做人的责任,在保持既有婚姻形式的同时,将爱示于新人,又担当起照顾前任的使命,如张恨水之于徐文淑、胡秋霞和周南;有的作家则在相濡以沫中,压抑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垂暮之年,才蓦然发现,难以忘怀的仍然是“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恋情,如林语堂;有的虽感恩于发妻彼时相伴的恩情,待到“头白鸳鸯失伴飞”后,偶遇新人,则爆发出常人难以理解的激情,如朱自清之于陈竹隐,梁实秋之于韩菁清;有的诗人,在空幻的诗文里寄予爱情的想象,加以婚姻的改造,希望在患难中彼此恩爱、相依为命,然而往往事与愿违,以悲剧结局,如朱湘与霓君;钱钟书是个例外,他与杨绛的结合,既是自由恋爱的典范,又是比翼双飞的楷模,堪称20世纪中国作家中“绝无仅有的结合”。
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张扬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婚恋观隐没在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时代潮流中。
追求个性解放、婚姻幸福为人生第一要义的婚恋观受到质疑。在民族危亡之中,儿女情长显得微不足道,集体化、社会化的婚恋观成为时代风尚。随着为民族生育的“优生学”生育观勃兴,沉溺于个人爱情幸福的主张日渐式微。左翼文人提倡文学武器论,使推崇个人情爱的“鸳鸯蝴蝶派”受到了严厉批判。
革命的洪流使个人情爱的意义,在集体化的婚恋观面前逐步消解。当一切都从社会整体出发,个人从属于社会,家庭只是社会的附属物时,个人情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缺乏了生存的土壤。
改革开放后,五四时期的个人婚恋观推陈出新,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又重新回归到社会生活。然而,因社会的急速市场化,中国人的婚恋观念也呈现出一种市场化倾向,婚姻业已成为个人利益的最大工具。此外,女性主义思想的再次苏醒,使更多的人去思考婚姻的本质。中国人的婚恋观念,就因此而呈现出极其复杂多变的状态。
正因为张恨水、林语堂、朱自清、梁实秋、朱湘、钱钟书等作家,他们的婚恋生活经历了20世纪婚恋观的急速变化,乃至于人们对他们婚恋生活与创作生涯的关联兴趣不大。
连朱湘的《海外寄霓君》的影响,也无法与鲁迅的《两地书》、徐志摩的《爱眉小札》和沈从文的《湘行书简》相提并论。然而张恨水可以多妻和平共处,胜似亲人;林语堂耄耋之年仍难以忘怀的初恋;朱自清忘不了发妻的贤惠又珍视新人的温情;梁实秋在发妻死于非命后又投入热情似火的黄昏恋;朱湘在穷困和世俗中,绝望于婚姻的平庸;钱钟书与杨绛一辈子的举案齐眉……
书写著名作家、诗人和学者的经历,远比解说那些张扬个性解放、婚姻自主,抑或主张个人情感让位于民族解放的芸芸众生的故事,更能形象地说明20中国何从办婚姻渡到自由恋爱的。
透过这些作家的婚恋历史和创作之路,或许我们更能洞悉20婚恋生活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感悟他们在婚恋生活中经历的阵痛和蜕变,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20世纪婚观迁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