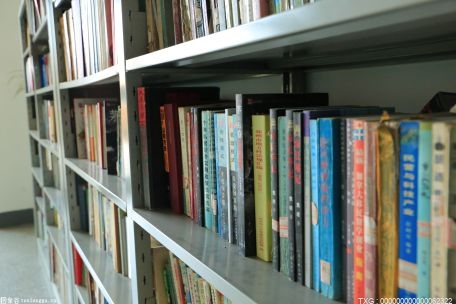“逸品”说的融贯性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上文指出,恽氏融会贯通,建立起达到逸格的探求门径:从锤炼笔墨工夫,到法古求新得意,到外参造化、中得心源,层层推进,渐入佳境。这种将美学概念互相牵引,融汇一炉,建立系统性诠释,也是恽氏绘画美学的特点。本文称之为“融贯性”。下文将通过对恽氏画论中“纵横习气”的内涵及其与相关概念关系的考察,继续深入讨论恽氏画学的这一“融贯性”特色。
恽氏论“高逸”云:“高逸一种,盖欲脱尽纵横习气,澹然天真。所谓无意为文乃佳,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若用意橅仿,去之愈远。”
这段文字直陈“高逸”之内涵,至为重要。以“澹然天真”为“高逸”,自属常义,恽氏有“纯是天真,非拟议可到,乃为逸品”之说,可互证。但“脱尽纵横习气”与“逸品”的关系,则有一层曲折需要说明。
清 恽寿平《藕花秋雨图》纸本设色 102.8×46.8cm
以脱尽“纵横习气”为臻于逸格的条件,不仅见于一处。如谓“方壶用米海岳墨戏,随意破颖,天趣飞翔,洗尽纵横习气,故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也”,与上文一致,可见“纵横习气”的破除在恽氏以逸格为统摄的美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以下画论提示了“纵横习气”的内涵:
“曾见石田翁拓为大帧,盈丈蔚然可观。尽其势,几不容于缣素,但过雄劲,似有纵横余习,未若王郎抚本,为冲和自在也。”
“巨然师北苑,贯道师巨然。贯道纵横,辄生雄犷之气,盖视巨然,浑古则有敝焉。”
由此可知,南田所谓的“纵横习气”,实为过于“雄劲”或“雄犷之气”之义。而第二条论江贯道作画失于“雄犷之气”,将我们引向以下这则画论:“贯道师巨然,笔力雄厚,但过于刻画,未免伤韵。余欲以秀润之笔,化其纵横,然正未易言也。”
明 宋旭《峨嵋万玉图》绢本 197×110cm
与上条相似,恽氏认为江贯道“笔力雄厚”,“雄厚”本非病,但太过则流于“刻画”,终致“伤韵”。用笔过于雄强而“伤韵”之说,又见别论云:“香山翁盖于北苑三折肱矣,但用笔全为雄劲,未免昔人笔过伤韵之讥,犹是仲由高冠长剑,初见夫子气象。”
“笔过伤韵”之说又有助于我们解释下一则画论:
“昔白石翁每作云林,其师赵同鲁见辄呼曰:‘又过矣,又过矣。’董宗伯称,子久画未能断纵横习气,惟于迂也无间然。以石田翁之笔力为云林,犹不为同鲁所许。痴翁与云林方驾,尚不免于纵横。故知胸次习气未尽,其于幽澹两言,觌面千里。”
赵同鲁批评沈石田临习倪云林,谓之“过”矣。这一“过”字,只有在“笔过伤韵”一说中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即用笔太“过”“雄强”导致“伤韵”,故不为佳。董宗伯称黄子久“未能断纵横习气”,故与“幽澹”之境相去千里。从恽氏“迂老幽澹之笔,余研思之久,而犹未得也”之说可知,“幽澹”正是对以倪云林为代表的“逸品”的描述。至此,散见于画论的诸多概念如“纵横习气”“雄强”“过”“伤韵”“刻画”等等,通过互为生发的解释,作为达到逸格的阻碍因素的诸多弊病,被恽氏融汇到一个完整的诠释体系之中。恽氏绘画美学思想互相发明的精妙诠释,可见一斑矣。
元 倪瓒《江亭山色》94.7x43.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
上文评价江贯道的画跋中有“余欲以秀润之笔,化其纵横”一语,则更将我们的视域扩展到臻于逸格过程中的积极性因素,即“秀润”的概念。以“秀润”化解“纵横习气”,道出了“脱尽纵横习气”的内涵。还可通过如下画论参证:“乌目山人此帧,画树师营邱,沙汀石骨用李晞古。笔趣清润,兼六如居士,盖所谓脱尽纵横习气,非强事点染者,所能彷佛也。”
以“清润”解释“脱尽纵横习气”,正与“秀润”之说全同。然则,“秀润”可以看做“幽澹天真”外,“高逸”的另一内涵,他评价“惠崇江南春卷,秀润之笔,臻为神境”,亦是一证。恽氏以“秀润”指示“逸格”,可由他对元人逸格绘画的解读相参证:“元人幽秀之笔,如燕舞飞花,揣摸不得。”“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种灵气,惟其品若天际冥鸿。”
这两条中恽氏一再指出元人用笔的“幽”与“秀”,恰可与前文辨析的“高逸”所具有的“幽澹天真”和“秀润”两个质量一一对应,这绝非偶然现象,而只能理解为恽氏绘画美学思想“融贯性”的体现。
五代 董源《溪岸图》220.3×109.2cm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以上通过分析恽氏异时异地所作画跋文字,发现他的“纵横习气”“雄强”“过”“伤韵”“刻画”等诸多概念竟然能够互为表里,交相发明;而构成“高逸”内涵的“幽澹天真”与“秀润”两个因素亦与其对元人绘画“幽”与“秀”的评价遥相呼应,若合符节。这类概念的组合并非特例,且随着引入条目的增多,其中包含的概念数量也将得到扩展。限于篇幅,不再条举。至此已经足够使我们推论出恽氏画跋的两方面特点:一是其绘画美学理论的“融贯性”。画跋文字虽然分散各处,内容也各取一面,但可以看出,其背后存在一个圆融的诠释体系。二是其绘画美学概念皆以“逸品”为旨归。无论概念是正是反,经过环环相扣的诠释,最终都指向“逸品”的价值祈向。易言之,“逸品”是恽氏绘画美学理论中统摄全体的核心概念。
“逸品”说体系的独特审美性格
最后,有必要对恽氏这一圆融诠释体系的特殊性格做进一步申论。
恽氏“逸品”说中,实际包含“苍浑”与“秀润”两个方面,不可偏废,而关键则在掌握二者的度,亦即不能“过”。其谓:“一峰老人为胜国诸贤之冠,后惟沈启南得其苍浑,董云间得其秀润。时俗摇笔,辄引痴翁,大谛刻鹄之类。痴翁墨精,汩于尘滓久矣。”
可见,高逸如黄子久者,实兼具“苍浑”与“秀润”二端,但后世画家即使如沈启南、董香光之卓然大家,亦每蔽于一端而不得兼综。以理论之,恽氏既以“逸品”为理想高标,则当直追古人,扣其两端而致其中,无所偏倚。但细绎恽氏画论却发现,他竟然自觉地偏向“秀润”一格。上文引述恽氏诸跋,皆以用秀润之笔化解雄强的纵横习气为务,已可略见此倾向。而其更云:“作家画,贵有士气,士大夫画,贵无作气。作家无作气固难,士大夫秀其本色。然恐人以规矩绳之,强为枯雄健举,不知已入作气,而时俗辄以为工。”
明 文徵明《空山夜雪深诗意图轴》
直接以“秀”为士大夫“本色”,且认为士大夫有“强为枯雄健举”者,则为入于“作气”,下诸一等矣。在摹古与创作实践中,恽氏亦有意地强化“秀润”风格。如其论临倪云林云:“以云西笔法,写云林清秘阁意。不为高岩大壑,而风梧烟筱,如揽翠微,如闻清籁。横琴坐忘,殊有傲睨万物之容。”
自觉地去除“高岩大壑”之雄,而求“风梧烟筱”之秀。又跋自作《五松图》云:“五松图,神气古澹,笔力不露,秀媚如妇人女子,然而骨峙于外,神藏于内。”甚至自求“秀媚如妇人女子”的用笔。相对于“苍浑”,恽氏更加偏爱“秀润”。实际上,“秀”正是恽氏存世画作的一贯风格,如秦祖永论南田画“落墨独具灵巧秀逸之趣”,亦是后世恽氏一脉的基本面貌。如郑午昌论钱杜云“其逸笔花卉,娟秀生动”,评陶淇写生云“资致妍雅,用笔柔和超逸,得南田、新罗神趣”,皆是其例。
恽氏不守中道而偏执“秀润”一格的原因,推测有两个方面:一者恽氏见时弊一味悍肆,欲有所纠正。下文会论及,恽氏画学始终以将时弊“一是正之”为己任。二者恽氏本身性情所衷,以“秀润”为长。
北宋 李成《乔松平远图》绢本墨画 205.6×126.1cm
三重县四日市澄怀堂美术馆藏
无论如何,我们都由此看出,恽氏绘画美学理论所包含的诠释体系,并非脱离时空的绝对中正持平之说,而是基于实践而有所偏倚、有所选择的“一家之言”。这使恽氏的绘画美学摆脱小大无遗、平正无奇的空疏层面,成为立足实践、极具个性的体系性学说。可谓偏至之处,正见独诣之妙。
恽南田的绘画美学以“逸品”说为核心,“逸品”说统摄全体,而诸多概念亦最终指向“逸品”之理想。因此,上文详细讨论恽氏“逸品”说的“实践性”与“融贯性”,二者实际上也是南田绘画美学的独到之处,亦即使南田画论在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史中占据独特地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