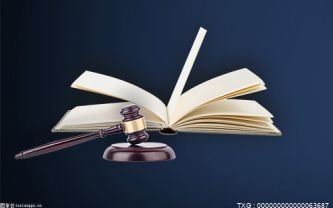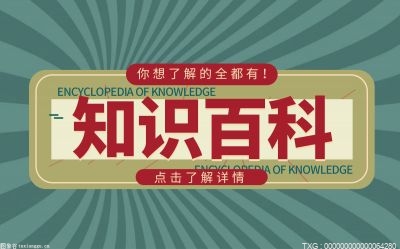在颠沛起伏的时代里,个体的生活容易显得弱小无力。时间长了,失望在滋生,抑郁在蔓延。如何在变幻莫测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安全感和生活的信心,成为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困厄。
但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带着热望活下去。
 (资料图)
(资料图)
如果你也陷入了这样的困顿中,汪曾祺先生的建议是去菜市场逛逛。
没错,菜市场是个能让人重新热爱生活的神奇场所。汪曾祺曾这样说道:“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普罗旺斯的夏天》
满满当当的货架,吵吵嚷嚷的家禽,人来人往,吆喝叫卖,讨价还价,所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流淌出热腾腾的生活。
一如先生爱去的地方,他的文字也是这样的“热腾腾”,鲜活的,朴拙的,能用幽默与风趣装点一切失序的生活。
汪曾祺
有读者会说,汪曾祺总是能够用一种很平淡的文字,一种几乎淡到连情节都没有了的叙事手法来写他的小说与散文,不正是因为他写的都是些安逸人生中的吃喝玩乐吗?恬静的生活自然催化出了淡然风趣的笔调。
但假如他的生活本身就非常戏剧性,在战乱之中、在动荡年代,他还能写出他标志性的朴拙、平淡和风趣吗?让我们来看看他如何写西南联大时期的故事。
在西南联大的生活,除了住宿条件简陋,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断炊,师生们还常受日军轰炸,空袭警报每天都要拉响好多次,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但在这样骇人的灰色场景中,汪曾祺却用笔调为我们解构出一番风趣的景象。
跑警报成了谈恋爱的好时机,因为这个时候女同学乐于被人照顾,男同学也正好献殷情。
《西南联大》纪录片
“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
他眼中也很佩服临危不乱的同学,跑警报时,学校的锅炉房没人,有人趁热水充足,炉火空置,便畅快洗头、高兴地煮起冰糖莲子来,生死也当置之度外了。
梁文道在谈到汪曾祺时曾说:在生活不能平静的年代,仍然坚持在生活中看到平静的味道,那就是一种对于这种不平静生活的抵抗与救赎。
汪曾祺画作
汪曾祺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身处时代的逆境,他却始终对生活保有一种热忱和洒脱。
在文学史上,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更因他对生活有着经久不息的浓烈趣味。就像他自己说:“生活是很好玩的——在哪里都能找到生活的趣味。”
写字、画画、做饭,明明平常普通的日常,他却深得其中的乐趣。“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在他的笔下,就连一草一木都灵动且富有哲思。
《人间草木》正是汪曾祺散文作品的标志,一部只收录花鸟虫鱼篇章的散文篇合集。一个平凡的景,经过汪曾祺的视角,便美得天真烂漫。在花草的散文中感悟汪曾祺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态度。
点击购买《人间草木》
一如他形容栀子花的名句: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 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这是一份恣意活着的态度,不仅要活着,还要用积极态度对抗一切悲哀。
他写葡萄,如何在四季的轮转中展现出强大蓬勃的生命力。
三月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地伸开,扇面似的伸开……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工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
十一月葡萄下架,“剪葡萄条。干脆得很,除了老条,一概剪光。葡萄又成了一个大秃子。剪下的葡萄条,挑有三个芽眼的,剪成二尺多长的一截,捆起来,放在屋里,准备明春插条。”
每一个月的葡萄都在不断改变自己的模样以适应气候。因为无论如今气候如何,来年它都得欢欢喜喜地发芽。
汪曾祺画葡萄
四季的葡萄就如同汪曾祺的一生,在历史洪流改让个人幽微的命运始跌宕时,他仍然带着虔敬的心扎根于生活。
作为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毕业后的汪曾祺却没能如愿名震文坛,甚至一度找不到活儿干。童年丧母,成长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又在本可以施展拳脚的年纪遇上十年动荡,大半生都颠沛潦倒。他的好友杨毓珉曾写过他的窘境:
“他(汪曾祺)已搬到从前周大奎住的那间五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真可谓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张三屉桌,一个方凳,墙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几本旧书。”
1958 年,汪曾祺被“批判”,许多年后他玩笑地说:“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实际上,那天他回家向妻子转述与领导的谈话时,“忍不住哭出声来”。为此他搁笔数年,“不写了,没什么好写的!”
汪曾祺与家人
可最后,当60岁的他重新拿起笔,写下一鸣惊人的《受戒》,却没有半点苦闷和忧郁,全然一副温情从容的闲适。他贪恋着人世间所有的酸甜苦辣,还保持着对生活骄傲的孩子气。
一如他写下对一草一木的观察。只有极度热爱生命的人,才能对生活有最细微的体察,才能在微小而饱满的事物中,获得底气和生活的哲理,因此,读汪曾祺笔下的花草,就如同看他在这人间的几十年。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
除了上文讲到的趣闻,栀子葡萄,《草木人间》一书中还有汪曾祺笔下的早春新柳,夏夜流萤,晚秋蝉鸣,冬日莹雪……时间流转、四季变迁,暂别凡尘,在花鸟草木之中感受生活之美,用花香虫鸣温暖俗世人心。
读一点他的散文,你会更热爱这个世界。
汪曾祺的文风干净清雅,像带着一股淡淡的桂花香。鲜少讲什么大道理或是批判,也很难在文字下看出什么隐喻。他总是用一种带着人文主义温情的目光注视世间万物,用平实的词藻——甚至夹杂些许方言,像着水墨的画,用极淡的笔触将故事娓娓道来。
文章中大都采用短句,节奏明快,烂漫洒脱。晚年时,他更追求大道至简的极致,在作品里彻底消解了故事性,他将目光聚焦在小人物身上,关注小人物在大时代浪潮中的命运。只用三两笔闲淡地勾呈出情景,结尾淡如炊烟,余味但击人心。
汪曾祺的一生颠沛坎坷,历经无数苦痛。回归平静后,他仍然没用辛辣的语调,没有歇斯底里,而是用一种朴拙甚至带着点童真的视角真去回忆描摹。这种平静像是他与自己所处时代的荒诞和解,但也是为了对抗或者说超越荒诞。
汪曾祺与沈从文
或许,正因为汪曾祺从未忘记沈从文的教导:“千万不要冷嘲”。这是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的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
汪曾祺的儿子说:“爸爸总是把最美好的事物展现给大家,把苦难的东西留在自己心里,因为他觉得,哪怕是再绝望的时候,他也一定要给一丝绝不会断绝的希望。”
“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想让我们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有诗意的。
今天,我们再读汪曾祺,仍能体会到仿佛置身三、四月的稻田间,暖阳当头的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