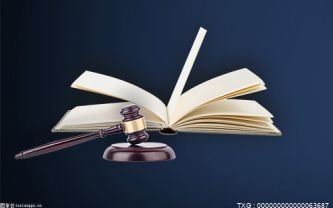倡导印面文字有书法属性,最早要追溯到明代的朱简,但真正把“刀笔并重”提纯为理论的篆刻家是赵之谦,赵之谦有代表性的理论,出自他的那方著名的“钜鹿魏氏”的边款:
 【资料图】
【资料图】
(赵之谦“钜鹿魏氏”及其边款)
其实,赵之谦之所以在这里强调“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的缘由,是因为当时的印坛为“浙派”一统,失去了发展的活力,而浙派的流派特征在于“碎切”,在于强调“刀”,也因为这个原因,忽略了“笔”。赵之谦认为一方好的篆刻作品,应当是“刀笔并重”的,既要强调“刀情石趣”,同时也不应当忽略“笔情墨意”。
篆刻以刀刻石,因为创作材料的原因,篆刻的“刀情石趣”是天然的,难点在于“笔情墨意”。要在坚硬的刀与石的交会中表达柔软的毛笔才能表达的书法意味。本文我们就结合一方印说说那些体现在细节上的“刀笔并重”,这方印就是陈师曾的“金石寿”:
(陈师曾的“金石寿”)
这方印的章法是汉白文印章法(陈师曾一直认为汉印的章法才是篆刻“正格”),三个字规规整整地摆在印面上,乍看之下,就是一方普通的词语印,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但它却值得我们认真观察,认真体会。
我们的关注点,应当放在它的“刀笔并重”上。
以刀刻石,由于石料的物理特性,几乎是必然会产生较为锐利的石材崩裂痕迹,这种痕迹,即便是熟练的篆刻家也无法完全控制,因为石料受刀后,因为施刀者用刀的力度、速度、角度的差异必然产生随机的崩裂痕迹,这种因种种“意料之外”而产生痕迹里,恰恰蕴含了篆刻特有的趣味(或者从某个角度说,石料的意外崩裂,才是篆刻的趣味所在),高明的篆刻家可以依靠经验和训练尽可能地“控制”这种崩裂,并结合自己的审美进行后期的细微“调整”(即后期的“做印”与整理)。
实际上,这种控制力和调整力以及审美能力水平高下是判定一个篆刻家是否高明的标准。
这种“控制”和“调整”是有选择的,其决定因素是篆刻家的审美选择,实际上,所谓的“刀笔并重”就是篆刻家审美选择的结果。
(刀与笔的差异)
刀和笔是明显不同的。笔的感觉更温润、柔和,其属性是阴柔的,它能呈现更多的“笔墨情韵”;刀的感觉更刚硬、凌厉,其属性是刚硬的,它能呈现更多的“金石之气”;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两刀相接,呈现出来的刀痕基本看不出施刀时序,即看不出哪一刀是先刻的,哪一刀是后刻的,因此,刀痕一般不能形成时序,而毛笔书法中的前一笔和后一笔是可以体现出顺序的,即哪一笔是先写的,哪一笔是后写的,因此,“笔”更易表达出时序节律,更容易形成节奏。
结合这方印来说——
一方面是历历刀痕所表达出的“刀情石趣”,或因为不加掩饰的崩裂而显得锐利,并由此促成了猛利之味,或者是因为行刀迅速而产生的光洁,形成的刚硬之态,这些特征,是以刀刻石所必然形成的天然“趣味”,这也是篆刻区别于书法的艺术特质。在篆刻作品中,这种“刀情石趣”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元素。
(历历刀痕所呈现出的金石之气)
另一方面,它还有经过有书法修养之后以刀痕模仿笔痕而表达出的“笔墨情韵”,有藏锋,有回锋,有特有的中锋行笔形成的线条两侧的对称,也有毛笔书法所特有的墨水形成的线条的圆润。
(模仿墨迹而表达出的笔墨情韵)
“刀”与“笔”是篆刻审美的两个支点,都非常重要,要在同一方印里保有这两种审美元素并不容易。近现代成名的篆刻家们,在作品中都非常重视“刀笔并重”。
当然,这一方印里,还有一点细节也需要特别说一说,就是笔画交接处故意留出的交接痕迹(虽然这是印从书出的“副产品”),有了这个交接痕迹,强化了书写意味,同时也增强了书写的时序性,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较深厚的书法修养。
(笔画交接痕迹与印面左右连结)
另外,这方印与标准的汉印还有不同,就是左侧的“寿”字中有一笔突入了右侧,并且与右侧的“石”字产生了连结,这是“文人印”与“实用印章”的区别所在,这笔连结,实际上使印面三字更加团聚,也使印面气息更加活泼。
(【布丁读印】之166,部分图片源自网络)